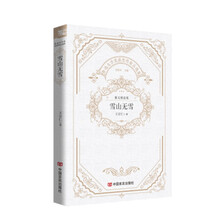虫子在唱歌
在西安这座城里,我在32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不足百平方米,但是样样俱全,一个人坐在书房,心中有掩饰不住的高兴。夜深人静,就连三环边的车辆也少了起来,小区各角落的虫子汇集起来,开长会,奏响乐,抑扬顿挫,有很多说不完的话。虫子的声音从窗外传来,跳进书房里,响彻于耳边,我顿感这房子也灵动起来,不仅有一本本书在架子上列队,更重要的有这些会说话能唱歌的小精灵们也在陪着我了,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他们就依附在我耳边说话。我听不懂,但是我心里变得高兴起来,至少这个世界里不是我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着,不分白昼与黑夜。尤其是黑夜里,他们就愈加显得兴奋了起来。
虫子一直在陪伴着我,走了这么多年。想起小时候我胆小如鼠,一个人躺在场院夜里的麦草垛上看粮食。漆黑的夜里,树影在风中晃动着摇摆不定,场院上鬼魅幻影,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我就用麦草把自己埋起来,顾不上麦芒刺入皮肤的疼,把自己埋得严严实实,只听见虫子一阵阵地说话。有虫子看管着满场的麦子,还有铁叉、木锨等一个个农具作为守护者,粮食就不会被松鼠们糟蹋,也不会被不自觉的人顺手牵羊,扛走一袋。当我听见有人们说话的声音,才敢探出头来,像个缩头的乌龟。离开麦地十多年了,我一直没有气力做好庄稼,我亏待了那一亩三分田的川地,那是河滩里最好的一块,这些年就那样荒芜了起来。荒芜地让人看着心疼。有人说:腰长脖子细,干活没力气。我在田地里,穿过小麦地,当人家都快收割完的时候,我还握着镰,手里却磨起了水泡。那是多么让人难以说起的时光啊。
突然这么多年就过去了,窗外的虫子还在一直在啾啾地叫着。他们住在院子的草丛里,唱累了,口渴了,就吮吸着后半夜落下的露珠。我的内心激动起来,是这座城市安放了我,虫子安放了自己。时间给我的恩泽,露珠成了大地对虫子的回报。虫子应该是个勤快的动物,他们白天也唱歌吧,人流不息,车流不止,只是被这世间的喧嚣掩盖了,虫子的脚步被人为地放慢了。虫子的嗓音是最好的,简直就是天生的丽音,它们就是为了不停息地给人类带来精神意义,才一直唱下去,直到死去,甚至连尸体也被其他生物蚕食,最后给这个世界没有留下一丝念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明年这个时候的我,可能还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着,脸庞会变得苍老,但是虫子呢,已经被新成长起来的后代们所代替。虫子虽长在城市,他们和我一样,角角落落地生存,我多么地期望它们就一直在我身边,能够收留我,接纳我,让我再一步步地靠近,倾听它们的声音,始终能做上他们最忠实的听众呢。
瓦瓮
“瓮里有面,心里不乱。”母亲常说这句话。瓦瓮者,陶制品,口小,腹大,是故乡家家户户用来盛磨好的面粉之佳具。
家里有高低不等、粗细不一的瓦瓮六个,在厨窑左壁的长条凳上按照大小一字排开。瓦瓮根据大小和当年的年景不同,里面装着黑白面粉。瓦瓮里面粉的颜色,是衡量当年家里生活水平高低与年度粮食质地和产量的唯一标准。那时候白面馍很是稀罕,听姐姐说,我出生时家里瓦瓮里的白面少之又少,仅够逢年过节打个牙祭。我早产,母亲上工,就靠蒸馍发的糊糊灌肠子。后来母亲四处开荒地,遍撒麦子,每年在收割时为了一粒粮食也要花很大气力捡回来。我一两岁时,家里唯一的白面馍都藏在瓦瓮里,上面盖上厚厚的盖子,置于高处。当我饿了后,姐姐就爬上去,取了下来用开水泡了,一口口地喂给我。我现在之所以不吃泡馍之类的吃食,有很大原因就是那时已经吃伤了肠胃,才使见了泡馍便不觉间满口发酸,难受不已。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