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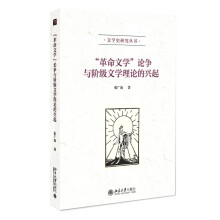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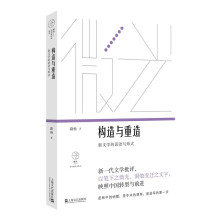


本书为我社2010年出版之《学术的年轮》的续编。作为学术随笔集,本书内容包括书评、学术丛札、学林随笔、怀人短札,以及为同事、友朋的著作写的前言、读书札记等,还有 对自己过往岁月的回忆,涉及评书、怀人、学术评论等丰富内容,是作者近年来学人随笔的结集,从中也可见出作者对当前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的深入思考。如同生长在原野的大 树,年复一年,铭刻生命的年轮,昭示生命的尊严和希望。文笔深入浅出而又不乏思考的深度,见性情,见学问,见阅历,用心良苦,颇可一读。
吹万集
如果说民众已经摆脱了一次高尚的愚昧状态,
并且受到表面光彩的迷惑,
那么,正像我所感觉的那样,
道路正在以令人厌恶的更加矫揉造作的形式往回走,
回到愚笨去。
——利希滕贝格续编吹万集·钱钟书的道义担当及其他续编钱钟书的道义担当及其他
钱钟书是永远的话题,也是吸引人的话题。浏览近年发表的钱学文章,感觉也开始出现以前陈寅恪研究曾出现的那种倾向,研究对象逐渐沦为话语符号,论者都借着谈论钱钟书来表达自己的某种观念。这也是很自然的,钱钟书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一个典型,无论其政治人格还是学术品格,都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一个类型。深入考察其生平行事和政治命运,不用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钱之俊《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一文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16日刊出后,迅速在网络上反复转帖,显出读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文章摘引我《在学术的边缘上》一文对钱钟书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的批评,认为“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钱钟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作者对我的批评,我并不在意,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立场。而且钱文作为历史研究,究明钱钟书幸未划为右派的个人原因,也是有意义的。但作者看问题的出发点及所流露的价值观,却让我感到一股浓烈的犬儒主义气息,而这也正是当今中国学人的普遍倾向,且与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相连系,值得认真推考。
首先要解释一下,我的论断有特定的语境,是讨论钱钟书算不算大师的问题。若是个普通读书人,他无论如何选择都无可非议,但作为大师,我认为钱钟书缺乏应有的文化和道义担当。这么说是有众所周知的特指背景的。有无文化和道义担当,不仅是衡量大师的重要标准,也是判定一个文化人是否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基本尺度。关于钱钟书的缺乏道义担当,我曾在《对〈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几点“声辩”》中有过陈说。“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胡适日记,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打学生,胡适做了什么;再想想毛泽东让陈寅恪当历史所所长,陈寅恪提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就很清楚了。”拙文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这些无名无望的年轻学人,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像钱钟书这样孚一时众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却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这绝不是大师应有的品格。
作为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又经历过“文革”以降的岁月,我当然理解他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我那么说,其实不是针对钱钟书个人,而是针对一种现象,一个现实,一个足以压抑和泯灭文化人的道义担当的严酷现实。如果钱文从“同情之理解”的角度谈论宽容,我当然无话可说,也可以同意。但很遗憾他不是,他说这是钱钟书的大智慧所在,并且说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这就让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了!若钱钟书是大智慧,那么储安平和所有右派是什么,都是愚蠢么?还有彭德怀,不更是愚不可及么?这无异是在说,在那种政治征候下,大家都应该知道进退,做出头鸟、出头椽子都是愚蠢的。更延伸一步,面对社会的迷乱,我们都不该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有机会表达,也要审时度势,看看这是不是个陷阱,是不是个阴谋。最好干脆做缩头乌龟,甘于曳尾泥涂,或像鸵鸟将头钻进沙堆。如果钱之俊先生真是这么想,那就不仅是对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英灵的莫大侮辱,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道义担当的价值践踏了!“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但在有英雄后,人不可以嘲笑英雄。
时至今日,连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反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自己都与有责任:毛被神化自己有份,毛的所作所为自己都曾默认甚至推波助澜;而许多老学者、老作家,面对林昭、张志新等人的事迹,更在内心为自己的愚昧、卑劣或软弱而羞愧。而钱之俊却称颂钱钟书的沉默是大智慧!我不知道钱钟书是如何看待张志新等人的,恐怕哀其不幸之余,还不至于庆幸自己有“智慧”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连称作知识分子也不够格,还谈什么大师不大师呢!如果不是那样,钱文的“智慧”之说,就无异于给钱钟书贴了一张并不体面的标签,恐怕钱先生九原之下也不会忻于领受的。他不会不知道龚自珍曾说过:“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据说他还说过:“‘文革’应该有三种羞耻:一种是受迫害者所感到的羞耻;一种是‘文革’打手所应该感到的羞耻;还有一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应该感到的羞耻。”最后一种羞耻他恐怕也不会自外于是吧?
说白了,钱钟书的处世原则也就是传统处世哲学——明哲保身,高蹈避世;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躲进小楼成一统。作为个人生存方式的选择,这无可非议,我甚至曾很欣赏。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放弃道义担当的正当理由和当然选择。如果文化人群体都奉明哲保身为处世原则,默认社会的一切黑暗和不公正,社会就永远不能进步。明哲保身毕竟是很自私的生活态度,人人明哲保身,整个民族就是一盘散沙、一群没有血性的懦夫。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多文化人事敌,那么多军人降敌做伪军,那么多平民面对人数少得多的侵略军毫不反抗,任人屠宰!归结到底,都是明哲保身的文化基因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多年前,学界曾展开一场主题为“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不前”的讨论,学者们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特征、自然环境各方面提出了假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士大夫群体及文化人阶层两种基本人格——与世沉浮或高蹈出世,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有关。尽管对现实有种种不满,只是著书立说,待王者兴,甚而仅仅是“腹诽”(到清朝这也成了罪),而不能挺身而起,拒绝或反抗黑暗的现实。
近代以来,虽然国体政体都已变革,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文化观念的变革却异常缓慢,现实也一再让文化人体会到传统处世原则的可贵。但这种观念和现实都是不正常的,也是媒体在日益揭开历史令人惊悚的黑幕之后,更强烈地激发人们反思的。钱文在揭示钱钟书幸免沦为右派的偶然因素时,不是抨击现实的残酷,却津津乐道钱钟书的“大智慧”,不经意中流露出作者所秉持的仍是封建文人那种传统的价值观。我所以对此斤斤较真,是因为这并不只是钱之俊个人的偶然议论,它实际上代表着知识界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前年我在台湾客座,读到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书。这是台湾知识界交口称赞的名著,但我读后却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快。与几位学界同道喝酒时,明知他们是齐教授的学生,我仍坦率地指出,此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已明显蒙蔽了她作为知识人的判断力和正义感。写到轮船上押送壮丁的惨景,没有对国民党军队非人道的谴责,只是用反战的态度间接地指斥共产党发动内战,而不想想一个政府要靠抓壮丁来继续战争,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正当性可言?更有甚者,闻一多等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言行和学生运动,都被视为盲目幼稚;对那些留在大陆的学者,言下处处流露出这样的意味:你们跟着共产党跑,最后有什么好下场?她不想,当时留在大陆的学者,虽然对共产党尚不了解、有待观望,但对国民党政府则肯定已失望之极。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齐教授在谈论那一代知识分子时所流露的一种优越感。在她眼中,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都是幼稚甚至愚蠢的,只有逃离政治和皈依基督教的她最为明智!作为个人选择,她远离政治的人生态度无可非议,但她那么评价闻一多们追求民主的抗争,就未免太轻浮,同时也太自私了。没有许多知识分子献身于抗战和民主斗争,包括台湾知识分子对蒋政府的抗争,齐教授未必能享有今天的民主和和平生活吧?一边享受着仁人志士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生活,一边哂笑别人愚蠢、以自己的高蹈为明智而显摆优越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齐教授的正义感和价值观。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钱文所显示的价值观其实折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群体放弃道义担当的现实。这一趋向在今天已非常明显,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是对社会正义、公民权利的无知与漠视;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则是对行政权力侵害社会公正和个人权益的种种现象的默认。许多人口不离民主,羡慕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但对几年一度的人大代表选举却漠不关心,或不参加投票,或随便画个圈,一边还抱怨没有民主选举!现行制度是赋予你选举投票的权利的,你有权利选谁或不选谁,结果你毫不珍视自己的权利。说到底,现实改变与否,社会能否进步,取决于我们是否有道义担当。但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道义感已丧失太久,以至于宪法将权利交给个人时,许多人都不知道用了。
更令人悲哀的是,当上海发生农民工的钱被风吹散、遭人当街哄抢时,公安机关对这公然抢劫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不立案缉拿罪犯,追究刑事责任,而媒体只是轻描淡写地要市民加强道德修养;北大博导剽窃抄袭,人赃俱在,而学生们竟齐声为老师喊冤;各种问题食品铺天盖地而来,媒体不是问责监管部门,反倒要人们多掌握鉴别商品的知识,变相提高人们的生活成本。知识群体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集体失语,已造成当今媒体舆论中社会公正和正义感的普遍缺失。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正义感等同于道德判断,这是很片面的。正义感是与道义担当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在于实际践行,与观念上的道德判断其实是两个层次的事。能践行必有观念;不能践行,有观念等同于无。我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收入《学术的年轮》)一文里,曾针对侯朝宗是否失节的论辩,表明自己的看法:“如此不耐寂寞的名士,应不应举,出不出仕,有没有气节,于人于己都是无所谓的。打个绝对的比方,一妇女遭强暴,一君子袖手在旁,以不助纣为虐为节操,可乎哉?为此,我对许多所谓洁身自好而其实无所事事的气节之士一向很鄙视。”明哲保身,在许多场合与洁身自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不在于有没有是非观念和道德判断,根本在于能否付之践行。而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践行的第一步。但明哲保身乃至洁身自好都停在了第一步之前。
大家都知道皇帝新衣的故事:谁都清楚皇帝的新衣是个谎言,但结束这一丑态却需要公开表达我们的看法。那个说出真相的孩子是践行者,而能否公开表达对现实的态度,也就是知识分子是否有道义担当的界线。曾有人举出钱钟书的某些诗作,认为他对现实是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的。这确是事实,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公开表达,也就同没有差不多。腹诽等于默许现实,默许现实便是缺乏道义担当。无论用什么理由为钱钟书的“智慧”辩解,都不能改变这一结论。对一个赚稿费混饭吃的小文人,这无须指责,但对一个被尊崇为文化昆仑的大师,我们有理由从这个角度质疑他。不是么?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4月3日)
00 / 钱钟书的道义担当及其他
00 / 有待开掘的古代文论宝库
0 / 清代诗学研究笔谈
0 / 就古代文论的“转换”问题答陈良运先生
0 / 就《清诗话考》回应吴宏一教授
0 / 对《渔洋诗:取于宋而归于唐》的一点回应
0 / 我对文学理论的技术要求
0 / 慎言“国学”一级学科
0 / 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当代武训
0 / 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投入
0 / 使用就是最好的保护
——在台湾第六届古籍保护与流传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振铎集
0 / 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2000年12月20日与人民网网友的对话
0 / 二十年学界目睹之怪现状之一:报销噩梦
0 / 二十年学界目睹之怪现状之二:经费怪谭
0 / 二十年学界目睹之怪现状之三:全民科研
/ 二十年学界目睹之怪现状之四:劣胜优汰
/ 探寻现代汉诗书写的另种可能
——关于近现代诗词研究与创作的对话
/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 关于“新诗与传统”的专题访谈
边鼓集
/ 胡大雷《〈文心雕龙〉的批评学》序
/ 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序
/ 张静《唐五代两宋诗法著述研究》序
/ 陶文鹏先生《宋代诗人论》序
/ 李昌集《文学史的认知与阐释》序
/ 李思涯《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序
/ 李世琦《申涵光与河朔诗派》序
/ 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序
/ 李雷主编《清代闺阁诗集萃编》序
/ 肖亚男主编《清代闺秀集丛刊》序
/ 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序
/ 王立《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序
/ 李春阳《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序
/ 刘鹏《中国藏书史研究论集》序
/ 张正欣《光影梦寻录》序
饮河集
/ 程千帆先生的学术品格
——读《程千帆选集》札记
/ 学古诗的门径
——读沈祖棻著《唐人七绝诗浅释》
/ 文学思想史:视角与方法
——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学术意义
/ 继往开来的学术总结
——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读后
/ 文献整理与唐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读《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札记
/ 学术史的另一面及其建构
——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略评
/ 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宇文所安《初唐诗》《盛唐诗》读后
/ 社会角色:一个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
——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者学习什么?
——《日本学者唐诗研究丛刊》前言
/ 我所采获的他山之石
——《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前言
/ 一个阁和一群人的元代
——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读后
/ 成为绝学:朴实与奢华
——扬之水《奢华之色》评介
/ 一部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
——读《清人别集总目》小识
/ 一部独具特色的清代人物年谱
——读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
/ 有待于重新认识的刘师培
——读万仕国编《刘申叔遗书补遗》
/ 由学术史回眸我们拥有的传统
——评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 学术史·思想史·批评史
——评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 游刃于文学史话语和文化政治之间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读后
/ 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略评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 历史也是个人的
——读许结《诗囚》感言
逝波集
/ 我的第一位学术蒙师
——赵继武老师散忆
/ 千帆先生手札二三事
/ 其学百代者,其品量亦百代
——追忆傅璇琮先生
/ 哭昌平兄
/ 在著作中永生
——追怀陆林兄
/ 有声有光的流星
——悼张晖
/ 批评家孟繁华酒事戏说
/ 我的高考1977·1978
/ 回眸学术的青春时代
——《大历诗风》写作记
/ 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因缘
/ 我的求学、治学与教学
——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刊》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