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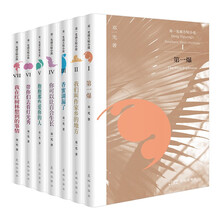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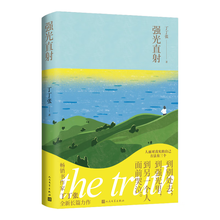




l 以饶有兴味的方式,发掘和重塑乡村人物的精神世界
l 巧妙的洞察与构思,讲述了鲁南乡村的信仰与传奇
l 百年前的乡村社会病,人物与命运的奇妙化合
l 深沉的现实主义画卷,透澈的民间叙事视角
l 集体的人格化表达,微观历史的强烈回声
l 用农耕社会的传奇,构造了美学意义上的陌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对民国乡村题材的描述
王兆军,山东临沂人,曾任《报告文学》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乡下人三部曲《白蜡烛》《青桐树》《红地毯》;散文集《皱纹里的声音》;长篇纪实文学《问故乡》及随笔集数部。作品《拂晓前的葬礼》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原野在呼唤》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把兄弟》获《亚洲周刊》2013年世界十大华语小说优秀奖。
因为这多出来的两庹皮线子,吴兴邦高兴了好些天。他到处给人宣讲自己的聪明,如何第一个发现三福的长处并加以发挥。他把三福的胳膊说得很过分,说皮货商人多么多么的懊丧,说他俩演的双簧何等巧妙,还说事后两人吃了锅饼喝了羊肉汤——其实只吃了个白面卷子——但他依然绘声绘色、得意扬扬。听者明知他的话里藏了夸张,但基本事实无法否认:三福的长胳膊确实长一些,兴邦确实因此多买了几庹好线子。不要小看多出的一庹线子,蚂蚱庙人对利益的算计可谓锱铢必较,即使多出一拃,也足以让他们兴奋几天!俗话说,苍蝇也是肉——蚂蚱腿也是肉,能多赚点为什么不赚?
在乡下,凡有实际好处的消息都传播得极快,三福的长胳膊一夜之间成了抢手货。村人凡要置办绳索或用到牛皮线子的,都会拉他一起去赶集。三福有求必应、腿脚麻利、反应灵敏,事情办得顺利圆满。此时,他的生理缺陷陡然变成众人传扬的优势,没人再称呼他长臂猴,也不再叫他二刘备,而改叫三福哥或三福叔了。春秋农忙前,总有很多人求三福帮忙。那些走进贾家小门楼的人,无一不是满脸堆笑,让三福感到充足的温暖和不掺假的尊重。后来,求他帮忙的多了,三福便有点拿糖,推说今日地里有活不能奉陪或腰腿着凉了走路不便,等等。来人便说:“等赶集回来帮你一起料理地里的活儿。”有些人还会带些小意思,几个鸡蛋、半碗萝卜干、一点点芝麻盐什么的……总不能白了帮忙的人啊。这里既有底层社会的利益交换,也有乡邻之间淳朴的人情味儿。
不仅这些。皮货市上的商贩们也对三福另眼相看了。最初,他们厌恶三福,恨他的长胳膊多量走他们的货物。有那么一阵子,谁见了三福都爱答不理的,甚至故意转过脸去装不认得。后来,这些生意人发现,凡是三福光顾的摊位,生意都好,于是他们对三福变得热情起来。三福一出现,许多摊主朝他打招呼,有的还送他几根旱烟叶。这一来,三福和很多皮货商人成了朋友。有些皮货商家有喜事,还会请三福陪客人喝酒,三福渐渐成了蚂蚱庙村的体面人。每次出门,他的腰里都掖着一条白色牛草包的毛巾,遇到邻人,他会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谁谁又请我去陪客了——我忙啊,不想去啊,可那边盛情难却,云云。从迅速扩大的人脉关系中,从各村商人和匠人的酒桌上,三福引申出更多更大的客户。半年之后,三福居然成了炙手可热的皮货经销商!一年下来,三福在方圆几十里都有朋友。他不仅从商贩们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类似提成),人也变得见多识广,待人接物显得老练而圆融。
三福如今成了蚂蚱庙的名人。二刘备的兴发,一时成为街巷间的话题。西酒店的大练长听说三福的故事,表示找个机会要见见这个人。在城里闹革命的小短辫也闻到三福的消息,也表示出很大的兴趣。谢芳春说,二知先生当年的预言应验了。看过《祝由科》的赵琪则怀疑三福的前生十有八九是个猴子。只有三福的老爹大襟袄对儿子的发达不以为然,甚至对乡亲们的夸赞颇为反感。他说:“从古到今,没听说靠两只爪子长就能混饭吃的。”三福对外界的评论淡然处之,褒贬由人,不置可否。吴兴邦多次央求三福,以后出去陪客不妨带着他也好见识一下各样人物。三福说:“人家没请你,我怎么好带你——找机会给你说个媳妇吧。”兴邦说:“你先给自己找个通腿的,然后再说我的吧。”三福说:“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愁没个媳妇。”
那以后,三福做了好多梦。他梦见一条龙从紫色云雾里飞出来,在蚂蚱庙上空盘旋,把他吓得魂不附体。等睁开眼,看见土墙缝里趴着一条蝎虎子。他很是纳闷:这小东西是那龙变的?抑或这蝎虎子刚才变成了龙?他以前曾经设想过油炸蝎虎子应当很好吃。自从有了这个梦,他觉得蝎虎子和龙也许存在亲戚关系,再也不敢奢望其为佐餐的美食了。还有一次,大白天,他躺在树下午觉,发现一位娘儿们从一片青纱帐里走出来,在他面前搔首弄姿。他一度怀疑那女子是变幻了形态的妖狐故意来迷惑他的,但他居然没有丁点儿反感。中间不记得发生过什么情节,蒙眬中好像蹭到那女子的皮肉,于是就有了异常的动作。醒来时,觉得自己魂不守舍,迷迷瞪瞪又困了片刻。再次醒来,发现裤裆里黏黏糊糊的,伸手一摸,状如米油。凑到鼻尖闻了,有点腥膻气息……
小吏狂语
在蚂蚱庙这样的弹丸小村,惊天动地的事情不常有,一个人稍有点名气,就会成为众口传播的新闻。近年在城里混事的赵建章听说贾家小子靠着两条长胳膊混吃混喝有点能耐似的,便有心想见见这个乡下小子。大约是人以群分吧,建章对这种不务正业的人好像有天然的兴趣。
现时说话,蚂蚱庙真正值得一说的人物,非赵建章莫属。几年前,赵建章宣扬大清气数已尽,号召大家起来驱逐鞑虏,光复中华,说四书五经那一套全得换成西洋的格物致知,考棚街上那些格子屋得一把火烧毁,所有男人的辫子都要剪掉,云云。很多人听了,以为他要造反,装作听不见的样子。没想到,仅仅几年光景,科举真的取消了,城里的私塾被洋学堂代替,考棚街的科举场屋虽没被烧,但确确实实是消失了。
世道大变,雨骤风狂,赵建章像个未卜先知的神人,居然能预见这么大的事!读过私塾的赵琪对他的同门谢芳春说:“院试没了,你做何感想?”谢芳春说:“俺本就没有贡生廪生的想法,识几个字,能看点闲书就够了。”赵琪素来看不上科举,就说:“还是建章有眼光。”谢芳春咂摸着嘴,问:“你跟建章熟,这么大的变动他是怎么预知的?他朝廷里有人?”赵琪说:“建章属于革命党,跟朝廷对着干的。他说用不了几年,皇帝也要倒号台。”谢芳春摇头说:“几千年的朝廷也要倒号?万不能的。甭听小短辫瞎说!”
小短辫是赵建章的诨名。蚂蚱庙有两大望族,一是村西头的吴家,家大业大,也有名望。居住村东的赵家,世代以耕读传家,祖上没出过显赫的人物。东西两大家历史上曾经有过不愉快,但阴影已被时光吹散。赵家兄弟四人,建章行大,小时上过几年私塾,后又捐过文秀才,总算个有身份的人。每当有人提及赵建章的乡约身份,西酒店的大练长都会嗤之以鼻:“他那也叫秀才?要说拿钱买功名,我能买个进士!”这话传到赵家,建章颇不高兴。乡约,听来是个虚名,但毕竟和整个体制有着首尾呼应的关系,算是体制内的人物呢。赵建章不是那种安心稼穑的乡农之子,他腿勤,待不住,东跑西颠,好像总在觊觎什么机会。他隔三岔五要到县城去,据说是履行乡约的职能。自古以来,乡村没有正式政府,县以下的民政管理大都付与乡贤士绅。乡绅一般拥有一定的财产,有家族势力作依托,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份为社会服务的热情和服人的名望。清朝以降,乡村两级有过或大或小的士绅机构,皆属社区性质,不在官府的正式编制。乡里设一名办事员,称为乡约。每村有个跑腿的,称为地保。乡约享有微薄的报酬,酬金从地方赋税中抽取,很少,也不稳定。地保则全无收入,其劳动属于志愿性质。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乡约名下那点酬金渐渐缩没,于是各县就把乡约和地保合为一体,两个称呼中各取一字,称“约地”。据说,他在城里认识了不少新潮人物,手里还有两幅当年县令——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字画。贾三福有一次在相公庄大集上见到赵建章,回村说建章大叔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跟了一位军官到三区巡视水利工程,那口气就像见到钦差大臣。
赵建章虽然顶了清朝“秀才”的身份,但他并不忠于满人。赵建章是蚂蚱庙上千号人中第一个剪了辫子的,而且公然宣称改朝换代要推翻大清的江山。那时鲁南地区没几个敢在清廷未颠覆前就剪去辫子的,剪了辫子等于自认是革命党。按照“留发不留头”的刑律,是要杀头的。赵家老先生发现儿子的头上没了辫子,捶胸顿足,大骂:“胆大包天了啊你!自打满人入主天朝,就有削发留辫的刑律,你一个大清秀才居然剪了……剪了!”赵建章应道:“世道变了。”老先生气急败坏地训斥:“再怎么变人家也是朝廷!满人不当皇帝了,自有别人去当。你就不能等人家都剪了再剪吗?啊!”为此,老先生一夜愁白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