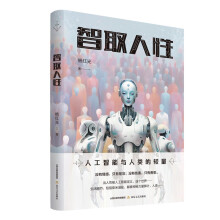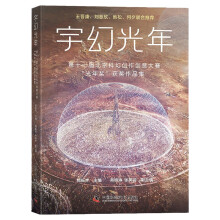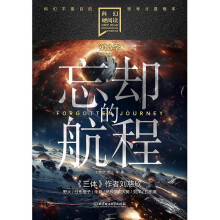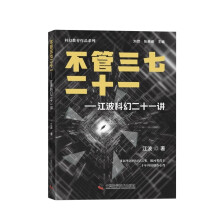《再见哆啦A梦》:
小学建在村口,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都来上学,曾经非常热闹,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分三四个班。但在我上到六年级那一年,一股去广东打工的风气突然刮起来了。大人去车间,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小孩悄悄地在黑屋子里穿线,每天也有三十块。这比在土里刨食要好多了。广东的厂家甚至派了车,停在村口,每天都有人带着孩子上车去往远方打工。村子就被这么一车一车地拉空了。
那时,一个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守在村口,拦着每一个带着孩子上车的大人,说:“你自己去就去吧,别把孩子带走了!孩子要读书,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读书,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人们都很不耐烦,推开老师。老师又紧紧攥住他们的衣袖,近乎固执地说:“别把孩子带走,孩子是未来,要读书。”
“读书能挣钱吗?”大人们反问,这让老师无法回答。于是,大人们把衣袖从老师手中抽出来,牵着孩子的手,上了车。孩子们低着头,不敢看老师。
那个漫长的暑假结束后,开学不到两个月,六年级的学生就从一百多个减少到了三十多个,老师也跑了很多。于是,原本的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由三个老师来教。教政治课的是一个姓丁的老头儿,每天干完农活儿来教室,给我们把课本念一遍,然后匆匆回去种菜;教语文课的是个年轻人,经常因为打牌忘了来上课,或者正上课时有人叫他去茶馆,他就放下课本跑了出去。
其余科目都是让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教,姓陈,独居,据说,就是她站在村口去拦上车人的。
第一次看到陈老师,我就心里一寒——暑假里,她站在坟场上看着我的阴沉眼神让我无比难忘。但这种害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快就看到了唐露。
唐露也和我到一个班上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胆怯孤单的小姑娘,之前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列,现在唯一成绩比她好的男生已经到广东的某个地下黑屋子里去穿线了。所以她现在是年级第一,被陈老师安排在第一排坐着,与我隔着大半间教室。
下了第一节课,我就跑到教室前面,但靠近她时又慢下来了。一种属于那个年纪的特有羞涩蒙上心头,明明没有人注意我,我却觉得自己处于所有异样目光的中心。她一直埋头做题,没有抬头,我慢吞吞地从她身边走过,也沉默着。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做题了。
两个月没怎么说话,暑假形影相随的日子已不真切,或许她也忘了吧。
其他男生也注意到了唐露。“刘鼻涕”有一次被分到她旁边坐,高兴得连鼻涕也不流了,就是上课看着唐露傻笑。陈老师揪了几次他的耳朵,都没用,只能皱着眉把他换走了。还有一向以欺负人为乐趣的张胖子,看到唐露和几个女生在操场上跳格子后,居然一反往常的鄙夷,上去请求和她们一起玩,还让唐露辅导他。唐露细声细气地告诉张胖子跳格子的要诀,他边听边点头,俨然好学生模样。陈老师看到后把他赶开,说:“怎么不见你把这股认真的劲儿放在学习上!”
陈老师对唐露严加保护,导致没人有可乘之机。除了唐露,我们所有人在她眼中都不学无术,都游手好闲,都是愚昧父辈的延续,都注定了要在这村庄里度过一辈子。
她严格按照成绩排座位,成绩差的都坐到了后面。杨瘸子提着两刀肉去陈老师家,希望她把杨方伟安排到前面坐,结果被陈老师轰了出去。第二天,她专门点杨方伟回答问题,杨方伟回答不出,于是,她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轻蔑地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拉不出屎来就别想占茅坑。”这句话一出,令我们哄堂大笑,杨方伟在笑声中脸红得如在滴血。
陈老师一度对我也寄予厚望。她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劝我好好学习,但当她知道我只对语文有兴趣,对数学课、自然课全然无感之后,非常惊异:“为什么你会对语文感兴趣呢?这是最没有用处的学问啊!真正可以拿来改变世界的,是科学,是对量子领域的了解,是对空间物理的掌握,一天到晚背几遍‘床前明月光’能有什么出息!”
她还说了一些什么,但那些词我都没听说过,只能低着头。她见我不开窍,叹了口气,就把我轰走了。
走之前,我突然愣住了——在陈老师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小木船,槐木雕琢,模样稚拙。我看了几眼,觉得有些熟悉,突然想起暑假我丢失在河面上的木船跟这个很像,连船篷的形状和上面的刻痕都一模一样,但仔细看又不对,因为眼前这个木船失光落彩,有些地方还腐朽了,像是已经摆放了七八年的样子,而我的木船沉进水里还不到两个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