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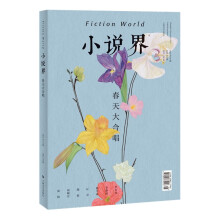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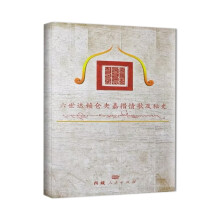
从不同的切面展示人们在这个时代所承受的痛苦与抉择。
在纷繁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如何找寻及确立自我?
也许在这本书中可以找见隐秘的答案。
回家
一整天,她都在地里采烟叶。下叶片清脆的剥落声总让她身体觉得疼痛,她说不清楚具体是哪个部位,是手指,还是僵硬的膝盖或者是吸进了大量烟气的胸腔。此刻,烟雾弥漫着全身,让她混沌不清。她不得不再次停下手中的活计,缓慢地走到烟叶地的边缘,坐在河滩上。一只枯瘦发黄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报纸包的烟丝,用卷烟纸哆哆嗦嗦地卷烟,她急不可待地将第一口烟吸进去,没卷紧的烟丝撒到了地上。
元江的支流打这边经过,现在是十月,水流像一股拧紧发亮的线顺着歪歪扭扭的河床流向远处朦胧的山峰。红色砂页岩的河岸裸露在阳光下,无数条黑色的裂缝像此刻她随着水流凝神望向山峰的脸。她高耸的颧骨上方堆砌着深深的褶子,棕色眼珠嵌在最深的褶子里,水流牵引着她迟滞的目光。她知道这河水打楚雄而来,经过玉溪、红河三个地州流向红河,再到河口县流人越南。
她曾顺着这条河流去过她认为这一辈子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八岁还是九岁?她趴在马背上,沿着河流,绕过哀牢山脉,路途遥远得让她以为这一辈子再也回不了家。见不着母亲,她还哭过。父亲是怎样趴在她耳边安慰她的,她已经忘记了。可是这一次,到了尘土都快淹没到她胸膛的年纪,她还要去一个更为遥远陌生的地方。她摇了摇头,在心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注意到地上刚撒落下来的细细烟丝,小心地捡起来,放进嘴巴,慢慢咀嚼起来。
她弯着腰把一整天采的十几捆烟叶背上了肩膀,宽大的粗布条紧紧勒着穿过腋下。她弓着背走路,双手不时地抓住腋下的布条来控制平衡,但还是走得摇摇晃晃。
西垂的太阳下,她像一个黑点在广袤的土地上缓慢地移动。她吃力地抬起头,连抬动眼皮都觉得吃力,背部的力量像在一路往下拉扯颈部到头部前额的皮肤,紧绷得像敲打中的羊皮手鼓。手鼓,在她心里呼呼呼毫无节奏地响起来。她舔了一下嘴唇,觉得全身干燥。家里的手鼓此刻正静静地躺在老伴身边,他脾气的好坏都能从催促她出现的鼓声的频率里得到断定。这一整天她多半也是为了躲避这个声音才去采烟叶,也是为了钱。
一季烟叶的采摘,可以换上几个月的生活费。
她已经走到了山坡,十几幢木结构的房舍立在山地的斜坡上,呆板地露出同一副开着小窗的灰面孔,竖着泥砖垒的烟囱,死死抓住地面,唯恐顺着斜坡溜下去。
“死气沉沉的地方。”她想起有一次返乡的儿子这样说过。
“这把老骨头背这么多东西,骨头会压碎的。”村口烟叶收购处的几个外来的村民看到她背了一座颤颤巍巍的山过来。
年轻力壮的收购员替她把烟叶卸下来。她跟过秤的收购商说,要结清这十多天来所有的钱,她要用钱。
她把几张钱反复数了几次,收购商的两片厚嘴唇吧嗒吧嗒控制着香烟,歪着嘴嘿嘿笑了两声:“老婆婆,我还能少了你钱不成?”
她摇摇头,神情尴尬地笑了笑,眼光瞟到杂货店到处缠着黄色的封箱胶带纸的玻璃柜台。她看过一次也是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电影,记不清名字喽,只记得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浑身缠满了绷带,只露出两只乌黑忧伤的眼睛。这个柜台就像那个伤员。她常这样想。柜台上,放着一部米黄色的电话机,以前是白色的。关于这一点,她一直清楚地记得。今天早上,她就是从这部电话机里听到令她浑身颤抖的消息,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血液凝结到一块,浓稠得化不开,几乎令她窒息。
她走到家门口,一条棕色的杂毛小狗从门缝里钻出来,走近她。它没有奔跑,看起来像是从薄暮中飘移过来的,一直到它蹭到她的脚边,好让她粗糙的手能够摸到它的脑袋。
P1-3
回家
山的另一边
挂在屁股上的钟
你要去哪里
去往海的另一边
搬家
失落的萤火虫
童年的最后一个夏天
下山
像鸟一样飞过天空
遥远的地方
如花美眷
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
胆小的人
十一叶常春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