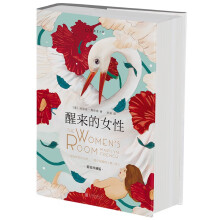凌时倚栏望着楼外的冷雨。走廊连着十间办公室,同事们进进出出,走过来走过去,开始还殷脸盈目“老凌早”“老凌好”跟他打招呼,稍后便专注于事、低眉垂眼疾步而过。他有一“毛病”,只要手有余暇便踌躇满志地拿着一根皮色斑驳的小木尺,一边拍着掌心一边来到走廊凭眺楼外景致。但这天早上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那一已随身40年的小木尺,而是一杯茶。这杯本是腾腾向上冒着灼嘴热气的浓茶,这时已成了年轻人夏日爽嘴的凉饮。
静悄悄的北风裹着黏绵的雨丝,时不时在他那已横着深浅两道皱沟的脑门上飘拂而过。在岭北,黏绵的春雨不是从天上下着来,是从辨不清的方向飘着来。它没有线,也不成片。它飘得整一个天似远似近、似有似无,让一切都成了灰:灰的岭,灰的树,灰的屋,灰的人。它一天接一天地悄然而来,再悄然而去。它不但黏滋滋,还潮乎乎;它不仅凉□□,还寒嘘嘘。这是让岭北人孵愁生怨的雨,也是使岭北人心灰意冷、万念俱寂的雨。他在岭北长大,没理由喜欢这雨,以往脸上若沾有这雨丝,他会一边用衣袖抹蹭一边诅贱它:“多余的东西。”但今天他没理会它,准确说他需要它,它那冻激寒乍的“提神”效果,远胜手里的浓茶。
昨天一早,公司关书记给他电话:“过两天你给大家讲讲你那书吧。大家有‘孝’概念没‘孝’内容,你给补补吧。”这电话让他兴奋一整天。在晚饭后的散步路上,他自言自语:“好嘛,这书你终于认啦。”他记得去年春节一过,出版社寄回书,他特地拿着来到办公室。关书记拿着书就像抓着一沓人民币,“唰啦……”用拇指在页侧上划了一下,一脸不屑,说孝啥孝,多往父母口袋装些钞票就是孝,然后摔在桌面上。“现在要我补上,嘿嘿,醒了。”他眯眼翘嘴,得意地边走边笑。今天一早上班,刚迈出楼道口,一头白发、脸皮皱塌并腰躬背驼的老母亲一见他,就两手撑紧那从不离身的四脚拐杖从花基边上站起来,将他堵在过道上,不管人多人少,不管脸面中看不中看,随性就嚷:“英曼这死婆,不给我冲凉,还说我吃她的饭不给钱,睡她的床铺也不给钱。阿霄这贼仔!老婆赶老母出门都不敢吭声。我不活了!我要去死!”一口气,不间断。她虽大岁已过85,但嚷声脆响且尖利,极具穿透力,直扎心肺,让他那昨天一整天积攒下的兴奋、自豪和喜悦,全跑没影了。
他困惑。平时起卧要人扶、下楼要人背、走路要人搀的老母亲,怎么就能来到自家楼下?要知道,那是一段公交车得跑三个站的路程呀。之前从没有过。他因此不知如何安顿她,只好不劝不说不吱声,随她嚷,只给她递去手纸。还好,她不哭。他从没见她哭过。过道窄,正赶上班,同单位的人多,熟。他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紫,又一会儿青一会儿白。有一阵子工夫后,她那脸上终于有了缓相,他便搀着她来到楼道口,好让她进家门后再作打算。但家在六楼,她往地上狠一甩手里的纸团:“你也想叫我死呀?我能爬上去,还会被赶出来?”他只好搀着她来到门岗,找了个凳子让她坐下。他给凌霄去电话。电话那头一阵惊呼:“哎呀呀,神呀,她能去到你那啊。哈哈哈!”晨练路过和买菜进出的退休老人,一个个都停住了脚步,将他和她围在中间看热闹。半小时后,凌霄开着自己的捷达车过来了。起先,已经不嚷不叫的她咋劝都不上车,说今天不走了,要凌霄回去把她的“家当”搬过来:“我不想再见到那个死婆!”后来一围观的老婆婆骂她:“你丢魂了?就知道嘴爽,你真要儿子喝西北风吗?枉长一脑壳白发!”她这才颤颤巍巍坐上车,但临走时摇下车窗给凌时甩出一句话:“我要阿宜服侍。”他杵在栏杆一侧,怔怔望着车子离去。
关书记说的“讲讲你那书……”是明天。书是自己写的,应该不费啥劲,但凌时啥事都先有一“畏”字。他本想利用仅有的一天将书再翻览一遍,好让明天的嘴巴更利索更巴顺,也让听众脸上能多挂点专注和欣然。但老母亲早上这一搅,将他的心思全给搅走了。于是他来到走廊,端茶倚栏望冷雨。
20年前父亲去世,凌时三兄妹在最初的40多天里每晚轮流回老屋陪母亲(这时候还不能称老母亲嘛)。有天轮到凌时,邻居赵妈悄悄跑来告诉他:“不行呀,每次阿玉回——回来,你妈深夜都会——都会哭。开始你妈哭,然后阿玉也——也跟着哭,整夜哭呀。”赵妈嘴拙,说话很难连贯。他不明白,他和凌霄回来母亲怎么就不哭?他问赵妈:“怎么我和阿霄回来,她的呼噜像拉风箱?”赵妈早年丧夫,年纪比他母亲大,个中缘由自然清楚:“阿玉不——不要单独陪了,你两兄弟轮——轮吧。”他告诉自己,不论怎么个轮法都不是长久之策!
凌时就此心悬了块至沉的石头。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