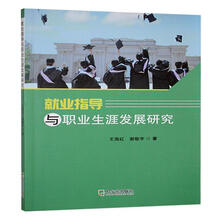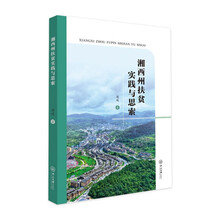“跑啥啊?穆少东家,小心地上滑,摔掉您老两颗大门牙!”时令才刚入初夏,年轻小子火气大,已性急地脱掉上衣,露出胸前两扇肋骨,也不管自己光着上身是否不雅,冲慌慌张张向前奔跑的小伙柱生高声嚷道。
柱生回过头,狠狠瞪了同伴一眼,两条长腿飞快地向前奔,还忙里偷闲地回骂他一句:“谁姓穆?你爹才姓穆呢!”
街上的熟人不约而同爆发出一阵欢乐的大笑。
这是看上去十分平常的一天,成都街道和往日一样喧嚣热闹。特别是在东大街,这儿商贾云集,卖货的买物的,人山人海,络绎不绝,骡马老板悠闲地坐在车架上甩着响鞭,轿夫额上青筋暴突地吼着“快点走,格老子的,莫挡到路嘛”,抬滑竿的汉子昂首挺胸,快乐地哼唱着一首他们家乡流传的小调。平时柱生最爱在街上游荡,东瞅瞅西看看,哪里热闹哪里有他,但今天他心里揣着正经事脸上的神情就格外不耐烦,恨不能从这些黄包车、板板车、鸡公车,从这些长袍子、短褂子、阔腿裤子间砍出一条通途来,他好赶紧一鼓作气跑回家,告诉穆老板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柱生今年十九岁,长着和圆团团脸的穆老板截然不同的长脸孔,身量虽不高大,臂膀上倒鼓凸凸地伏着几坨肌肉,暗暗运气,肱二头肌能像被柱生驯服的小老鼠,乖巧地在他手臂上轻轻走动。凭着这身肌肉,柱生在东大街上也没怕过谁,哪个敢惹他?小爷奉陪!大不了就是一个“打”字,男子汉大丈夫,怕个甚?
柱生不怕挥拳头,也不怕被人家用拳头招呼,但怪得很,他莫名有些怕穆老板。不过几年前看他懂事了,骨架子拉开了,在街上和混混流氓打得鼻血长流也不吭一声了,穆老板便不再像之前那般对他婆婆妈妈,“好好读书”的话翻来覆去能叮嘱一万遍。到底从哪天起呢,穆老板看柱生的眼光变得平和了,言语也寡淡下来,父子俩有时坐着闷头吃饭,一顿饭吃完,谁也不说一句话,安静得像两个聋哑人。
现在,柱生没时间细想穆老板是从何时开始对他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客气的,他急急忙忙跑进大丰米行的大门,差点被倚着门槛打瞌睡的花猫绊了一跤,伙计白脸亦吓了一跳,问柱生青天白日是不是撞到鬼了?柱生来不及喘匀一口气,鼻孔呼呼拉风箱,指着店铺柜台的高板凳,拿手势发问。白脸到底是聪明人,很快理解了柱生的意思,摇头道:“不晓得今天你们两爷子咋的了,刚刚绸缎铺的马老板、竹编店的张掌柜都来了,跟咱们穆老板咬了下耳朵,三人一起出门了,喏,你看咱掌柜账都没算完,有啥家国大事等着他们去商议啊……”
柱生没时间跟白脸啰唆,一个小伙计哪里懂什么家国大事,和他扯也扯不清楚,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穆老板!柱生转身又往外跑,既然马老板、张掌柜都来了,他心里有了底——这几爷子肯定是去了“锦春茶楼”。
锦春茶楼妙就妙在有个牛皮哄哄的茶博士,每每茶客一落座,刚点罢茶,茶博士便已麻利地提起一把亮锃锃的紫铜茶壶,左手像耍杂技一般,卡着一大摞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茶盖,摆起了架势。
茶博士虽算不上相貌堂堂——天生一张白麻子脸,沟壑纵横,却自有一股威严自信的态度。茶博士含了三分浅笑,趋身上前,就像武林高手过招,还没待茶客回过神来,只听耳畔“哗啦”一声响,十几二十只黄铜茶船已飞快地搁到了各人面前,那些生瓜蛋子忍不住“呀”一声,嘴巴还没合拢呢,茶博士手中的“武器”缓缓一点,紫铜茶壶犹如谦卑鞠躬,滚开的水已从茶客的脑后、肩头、耳畔唰唰射出,如一道悠长银线,从两米开外的地方准确无误地注入茶碗,根本不会有一星半点儿洒到外面。
最后,茶博士抿着嘴,收起茶壶驱前一步,用小拇指将散在桌上的茶盖往上轻轻一挑,只听得“当当”几声,这一二十只茶盖如同听话的小娃娃得了指令一般,忙不迭地纷纷跳起脚,乖乖地盖在了茶碗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