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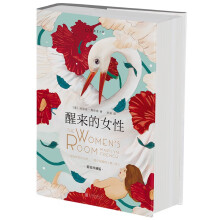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世间情愫三种,便唯有亲情,因血缘的恒固,无法自由选择。我们便也心安理得,一边沉默地付出给予,一方懵懂地被动接受。翻开本书,阅读作者笔下孩童时期成长过程的家庭生活琐事,感受三代亲人之间平凡又深沉的爱。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住进爷爷奶奶家,原本不幸的单亲家庭由此变成吵吵闹闹的“三亲”之家。慈祥的爷爷、强势的奶奶、倔强的老妈,还有总爱捅娄子的我,在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中一点点磨合,互相理解、扶助,奏响了一曲有笑有泪、大小调极速转换的生活协奏曲。
第一章你们说说,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
我爸去世后不久,供暖季进入尾声。
北京早春的风抬起袖口,像邋遢大王抹鼻涕似的捋着白颐路边高高低低的屋檐,将那些倒吊的冰凌冰锥,一股脑儿扫了个精光。只是刮到人脸上,依旧会沙沙的疼,尤其刚哭过以后,小脸蛋儿立马就被吹成两个通红的灶眼儿。我妈回昌平家属院歇了几天,又去厂里办了病退手续,然后提着个干瘪的尼龙布包搬来爷爷奶奶家,挤进我那九平方米的小宇宙,自此公转自转,成为这个“三亲”家庭中的正式一员。另两位成员自然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了。
我爷爷当时刚离休不久,每天依然精力充沛,不是上颐和园遛早,就是去紫竹院唱歌。半张脸大的韭菜盒子,一顿饭至少能吃五六个,最后还得再来两碗棒子面粥,北京话管那叫“溜溜缝儿”。某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在马路边剃了个大光头,回家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俨然变成《神雕侠侣》中宽厚仁慈的一灯大师。
要说我爷爷是一灯,那我奶奶就是体重加倍的灭绝师太。对不起,我知道我串戏了。我奶奶这人长得有个特点,腮帮子老是气鼓鼓的,不管什么场合总觉得她好像在跟谁生气。也是凭着这股子气性,退休后又成了小脚侦缉队里的大脚总管,每天到七区居委会主持日常工作,为四化建设保驾护航。
老两口当时面临的唯一难题大概就是我的学业了。再过半年,我就要升入六年级了,功课难度如同当时北京市民的申奥热情,直线飙升。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一向不赖,可人家重点中学也不是福威镖局,岂能任你说进就进?二老苦于能力所限,水牛抓跳蚤,有劲使不上,于是和我小姑商量一番,决定拉我妈过来救火。
那时候,我妈身体尚好,有点小病小灾她自己从来不当回事。偶尔,心跳蹿到每分钟一百二,脸色煞白,手脚齐刷刷冻成四块冰坨,可也就是含几粒速效救心丸,躺在床上做一番深呼吸,起来继续忙活自己的事。有时,半夜胆结石犯了,疼得身体扭曲,接近孔雀舞造型。我醒了问她:“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她照样中气十足地回我:“没事儿,睡你的觉。”我就翻个身继续睡了。
不是不关心她,但是我说不出口。从小到大,我都说不出关心别人的话。这是受谁的影响呢?我也搞不清。反正对于十一岁的我来说,帮助家人驱逐病魔的最好方法就是赶紧闭眼入睡,因为每次清晨醒来,我妈都会重新变得生龙活虎。
就这样,四个人,三居室,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日子像拧不紧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往前流淌。然而,这样的平静仅持续了一个星期。有天夜里,我忽然发现我妈又添了个新毛病。这病白天没事,晚上才发作,而且比胆结石严重,比心脏病更吓人——她竟然开始梦游了!
我小时候睡觉挺死的,一般来说,“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量是吵不醒我的。可偏偏那段时间,楼上新搬来一个大姐姐,每晚十点准时开始练钢琴,焚膏继晷,天天不落。琴声一起,别说“大珠小珠”,恨不得连“玉盘”都给砸了,自然就把我惊醒了。
小屋里刚停暖气,窗外还刮着呜呜的夜风。三月中旬的北京城,春天刚一露头就夭折了。我捂着自己冰凉的鼻尖,哆哆嗦嗦地跳下床,准备去“嘘嘘”一下。扭头发现对角的单人床上,被子偎着枕头一团萧瑟。
咦?我妈呢?
我们家三间房,由一条细长的过道连缀在一起。最大的那间靠东,是一灯和老师太的寝宫。最小的这间居中,我和我妈住。门外则是厨房和厕所深情对望。最西边还有一间中不溜大小的房间,算是“多功能室”,放着电视,支着餐桌,摆着沙发,倚着落地灯,立着高低柜,摞着两个红木大箱子,还挤着一台老式唱片机。高低柜好比东岳,沙发就是西岳,落地灯是南岳,唱片机就是北岳,至于那两个红木箱子,无论摆在哪个位置,永远是当之无愧的中岳,中岳嵩山嘛,五岳剑派之首。箱子里放着我奶奶的各种宝贝物件,没多金贵,却地位尊崇,谁也不敢轻易去碰。这间房既是饭厅,又是客厅,又是储物室,又是会议室,还是放映室和音乐厅,一专多能,自由切换。
我妈此时正背对着我,像一尊逼真的蜡像凝立于那台老唱机前若有所思。忽然,这个蜡像动了起来,抬起两只手做出一个挪动老唱机的动作。虚空中,那台老唱机仿佛真的就被她挪走了,冒着仙气,飘浮到一个虚幻的格子里去了。然后,我妈又像指挥交通似的指了指红木箱子,又指指高低柜,红木箱子和高低柜便也听话地缓缓升至半空。这边这边,那边那边,哎呀不对,往后往后,也不对,再往前来一点。老唱机、红木箱子、高低柜在那个虚浮的黑漆漆的十字路口,像三辆愣头愣脑的大货车,疲于奔命,往来辗转,还个个带着酒驾嫌疑,一不留神就会发生碰撞剐蹭。我妈有点不满意了,嘴里“啧”了一声,于是悬在空中的幻影复归其位,仿佛如来佛祖五根胖胖的手指,刚刚被奋力掰开一点缝隙,紧接着又牢牢并拢在一起。我妈摇了摇头,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对眼前这些不给力的“群演”。窗外幽暗,小风汩汩地流,把月光洗刷得异常清冷,半拉的窗帘像一块皱巴巴的幕布。我妈单薄的背影就在这幕布下晃来晃去,好似正在排练一部晦涩艰深的单人哑剧,气氛神秘而诡异。我站在房门外,揉揉惺忪的睡眼,确定自己不是做梦,便小声叫她:“妈妈,您干吗呢?”
我妈没理我,连头都没回,嘴里又“啧”了一声,好像陷进了更深的泥潭。楼上的钢琴忽然换了曲目,“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完全是砸锅卖铁的感觉,听起来怪瘆人的。
我畏缩着又叫了一声:“妈妈?”
我妈还是没回头。琴声继续在头顶肆虐,“当当当当”“咣咣咣咣”。
突然,我妈像是要钻防空洞似的,矮身跪在地上,还把手伸到老唱机下面,摸摸这儿,又抠抠那儿,最后干脆一头探下去,歪着脑袋,扫视起那片狭小黑暗的区域,也不知道在发掘什么。钢琴声从“砸锅卖铁”转为急迫的“大水漫灌”,好像一群野猪奔跑在泥巴地里,啪叽啪叽的。我猛然想起课外书里讲的,有关主人公梦游的段落。大意是说,遇到梦游的人,千万不要和他对话,更不要轻易叫醒他,不然会损伤到对方的脑神经,严重者甚至会变成痴呆弱智,连自己爹妈儿女都不认识了。想到此处,我心里也跟碰翻了一摞“玉盘”似的,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一不留神害了我妈,厕所也忘了去,直接跑回屋钻进了被窝。
窗边的暖气管上挂着个色彩缤纷的小泥人儿,是个奋起千钧棒的齐天大圣。那是前两年春节小姑在地坛庙会上给我买的,如今虽然早已风干了身段,但神态依旧栩栩如生。黑暗中,一对火眼金睛居高临下地瞪着我,鬼魅飘忽,蠢蠢欲动,仿佛马上就要去大闹天宫了。我赶紧闭上眼,脑子里“刷刷刷”蹦出来的全是电影里的梦游场景:《虎口脱险》里的奥古斯托,《神探亨特》里的精神分裂杀人犯,《寻找魔鬼》里弄丢藏宝图的鲁大刀……想着想着,杂乱无章的琴声、风声,都渐渐变得缥缈迷离。快要睡着时,我迷迷糊糊感觉我妈回到了床上,脸朝着墙,没一会儿就打起了小呼噜。
第二天轮到我值日,我妈还没睡醒,我就早早出门了。在学校门口排队买煎饼时,碰上了和我同组的女生兰天,我就把昨晚的梦游奇遇记给她讲了一遍。
兰天瞪大眼睛问:“真的假的?”
“骗你干吗?都快吓死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
“你妈妈是不是发现什么宝藏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奶奶家能有宝藏?你瞧瞧我爷爷袜子上那些窟窿,都快成北斗七星了。”
“扑哧!”兰天笑起来像个洋娃娃似的,接过师傅递来的煎饼,说:“等我中午回家问问我爸,我爸懂这个。”
太好了!兰天他爸是化学所的研究员,每次开家长会都拿个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做记录,一副很博学、很严谨的样子。
下午第一节课前,兰天果然跑来向我汇报:“我爸说了,叫醒梦游的人并不会变成痴呆,没有科学依据。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领回床上继续睡觉,不然的话,万一开窗户从楼上跳下去,或者无意中打开了煤气,那你家可就危险了。哦对了,我爸还说,有的梦游病人可能会用凶器自残,这你也要多加小心。”
我的妈呀,太严重了吧!听她这么一说,我更慌了,恨不得立马骑着班里的扫把飞回家,下午的课都听不进去了。班主任在语文课上讲解“绝伦”这个词的含义和用法,还给大家举例造句:“安徒生先生的童话故事写得精彩绝伦。好,下面谁用‘荒谬绝伦’来造个句子?”
马老师扫视一周,见我正坐在窗边走神,就指着我说:“李炀,你来。”
我根本没走脑子,不就是“绝伦”嘛,马老师用安徒生举例,我就用契诃夫呗:“契诃夫先生的每一篇大作几乎都荒谬绝伦。”
哈哈哈哈——全班都笑喷了。
第一章
你们说说,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 001
第二章
算了算了,不算了又能怎么办? 031
第三章
以前你要是这么说,我肯定不信! 065
第四章
多大的人了,还不敢自己睡觉啦! 097
第五章
真摔一下子,够你喝一壶的! 131
第六章
你干什么正经事了,就让我鼓励你? 163
第七章
咱爸哄咱妈也有三板斧,保证药到病除! 199
第八章
把炀炀送进重点中学,然后你想走就走吧! 233
后记
有些爱,你不说我也知道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