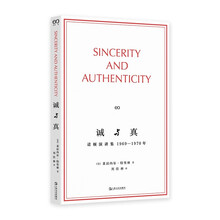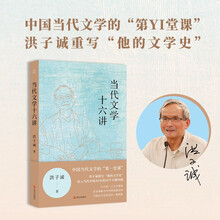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反对派研究》:
甚至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具体思路上,二者也体现出高度的融合。新儒家一部分代表人物,提出一种极具价值又很巧妙的区分:儒学与政治化的道德说教的区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价值传统与具体制度、习惯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与作为中国文化共同价值系统的区分。儒家的一些价值原则需要肯定和继承,而对于与权力、时代相联系的具体的儒家道德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批判的要批判,该舍弃的要舍弃。在启蒙主义中同样出现了这种区分。晚年的殷海光认识到,社会必须有道德规范才能维持,而“为了道德功能的持续,即令一个道德传统只有残余的功能,也须任其发挥,以待给它以充实的内容与新的活力”。应该把道德原理与具体道德分开,尤其是要把道德与现实层面的权力分开。这个基本思路被殷海光的弟子们总结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其实,这与新儒家的思路不谋而合。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互相影响的关系,但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二者对传统的态度出现了某种共识,出现了某种超越二元对立,相互融合的趋势。
这种趋势必然带来一些新学术视野。比如,秦晖是当代偏向自由与启蒙的代表性人物,但其学术主旨讲的却是如何把儒家的一些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由思想联合起来,解构中国法道互补的秦制传统。这种学术思路实际上就解构了“西方=现代、中国=传统”的陈旧思维模式。在老式思维模式中,喜欢传统的人就说现代文化是西方的、外来的,不适合中国的;喜欢现代的人则说,现代的民主自由价值来源于西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这些价值的反面。前者批评后者是贬低民族、背叛民族,后者批评前者是拥护专制。而实际上,被批判者都觉得受到了歪曲或冤枉。通过打破这种二元思维,一些无谓的意气用事的争论得以避免,一些富有建设性价值的讨论开始出现,一些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也逐渐变得清晰了。比如说,有人很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按照当代西方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世界上各个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无所谓高低贵贱的。那么对于任何文化的批判是不是都是一种文化歧视或西方中心主义?支持文化相对主义是否必然要支持本民族的任何传统?如果按照僵硬的二元对立,这个问题几乎无解,但绕开二元对立,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秦晖的办法是把文化与制度进行区分。文化没有制度意义,是无所谓优劣的纯粹的审美符号。比如,“中餐与西餐、英语与汉语、唐装与西装、过圣诞节与过春节都是‘文化’,中国的龙、日本的樱花、西方的十字架与阿拉伯人的新月等各自能唤起人们审美认同的符号也都是‘文化’,它们都不可比”。在此意义上,文化只不过是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偏好而已,而谁也不比谁高级或先进,所有文化都应该是宽容与平等的。相对的,制度是有优劣之分的和可比的,比如说是否尊重个人选择,是否维护个人基本权利与个性,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冲突时是否以契约原则解决等。在这种细分之下,我想大部分持启蒙立场的人也不会反对这种风俗习惯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也多半不会再反对这种尊重个人并兼顾群体利益的“现代制度”吧。
如果我们跳出二元对立的固定思维,再看对后殖民批评的民族主义相关批判,就会多出一些新的思考。民族主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有的合理成分多些,有些不合理的成分更明显。因此我们对中国当代的后殖民批评的不同议题不能一概而论,对待同一议题的不同倾向也要分析。当他们说第三世界批评与中华论者有明显的权力话语的痕迹时,大体是对的,但把所有的张艺谋后殖民批评者、“鲁迅国民性议题”批判者与前者归为一类时,则是偏激的。当他们批评“失语说”的发起者的各种问题时可能是正确的,他们批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中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主导建设当代文论时,也是正确的,但他们把所有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者都说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反现代化的或权力投机主义者时,这又是偏激的。
在强调中西的意识形态对立、排外、排斥现代性方面,“第三世界文化批评”与“中华性”可能有更多的“官方民族主义”成分,前者强调中西对抗并公开争夺话语权力,后者强调以中国文化为中心重建东亚新秩序的论调甚至有扩张主义成分,这种民族主义的确是需要更多警惕与批判的。它们与文化、审美少有关系,与伦理也少有关系,而是权力与政治战略,而这种缺少伦理支撑的战略只能是纯粹的丛林法则式的现实主义。确实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这种民族主义有一种好意作对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上会引发严重的价值危机与民族对抗,而在国内则过于顺应强大的国家权力,缺少批判性。另外,过度的政治化使它显得生硬而缺少学术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