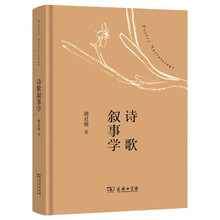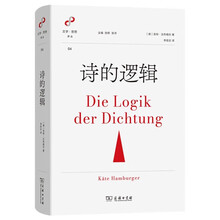而在建立联系、发现故事的同时,茅盾毫不客气地将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政客、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各类清客和帮佣……简言之,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海的几乎一切阶级,都封闭在“子夜”里。略有些费解的是,大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似乎一直安然无恙,周仲伟、吴荪甫也次第在买办化之后从困境解脱出来。然而,叙事者以不断驱动人物讨论中国命运、国家权利、帝国主义、爱国等话题的方式避免了不必要的认同暧昧,同时暗示着要获得未来,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在如此全景式地呈现上海各阶级末路的中途,叙事者开始以越来越多的篇幅叙述裕华丝厂女工的罢工运动。《子夜》第一至九章中,只有两章以工潮问题为核心情节,第十至十九章却有六章以工潮问题为核心情节,而且还直接叙述了罢工的组织过程、领导者的努力和女工的觉悟。这意味着《子夜》意图暗示,只有在全景式地呈现了各个阶级的状况,标识各个阶级的末路之后,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而解放的路径,就是集团主义运动,只有集团主义能构建远景。大都市上海因此被压缩成阶层分明的客体,小说形式的完整性在碎片中拼合出来。
相比之下,穆时英的虚构上海显得“不结实,不牢靠”,彻底碎片化,黄震遐在《大上海的毁灭》中虚构上海的方式也过于简单。黄震遐以书信来往的方式构建十九路军抗日与上海都市生活的联系,并且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分出两种人:“租界,好像一道万里长城似的,划分开这两种的人类—— 一面是演说,争辩,谩骂,而另一面则为牺牲,流血,奋斗。”这种划分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确实过于简单地将上海劈成了两半。而且,与穆时英的虚构上海有类同之处的是,黄震遐也耽于描写上海都市的声色繁华,如详细描写露露的肢体,这些描写很难说是小说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比照中,茅盾《子夜》宣示下层阶级兴起的诗情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卢卡契曾说:“作品中盛行的描写不仅是结果,而且同时还是原因,是文学进一步脱离叙事旨趣的原因。资本主义的散文压倒了人的实践的内部的诗,社会生活日益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这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从这些事实必然产生描写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一旦存在,一旦为重要的、有坚定风格的作家所掌握,它就会对现实的诗意反映产生影响。生活的诗意的水平低落了,——而文学更加速了这种低落。”穆时英尽管有坚定风格,但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茅盾则恰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引领了重要的小说传统,因此不能不说虚构上海的研究,并未完全成为资本主义散文的研究,有其重要的历史依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