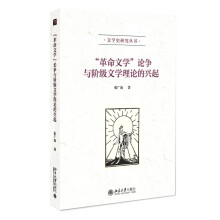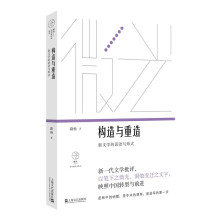《走向建构的对话——<应物兄>评论集》:
李洱是一个对言谈情有独钟的叙事者:受词语之蛊,逞口舌之快,潜沉默之语,让不同文体在记忆的纷争中解体,又在凭吊昨日之情感中有所建树;既有真言也有妄语,既有狂欢式的倾诉,也有冷峻的滑稽模仿,滔滔不绝演绎枝蔓横生,喋喋不休解读盘根错节,间接引述连接着间接引述,令人困惑的杂拌,蓄意中断的并置,不同文类的精心布局,对他者言语的随意一瞥,失去言语的潜伏,希望和绝望的沉思。他强调口述体的生命力,也不乏对书面语的推崇。言谈即描摹,肖像画和自画像兼而有之,正面、侧面与背影齐头并进。《应物兄》写下了众多人物,对叙事者而言,有些人是他推崇倾心的,甚至是心仪爱慕的;有些人是鄙视但不乏心中的恐惧;更多的人他的态度是暖昧的,他看他们的眼神是游移不定的。李洱的面部表情泄露了其叙述的风格特征,这使我们想起雨果对拉伯雷小说风格的看法:“严肃的前额下是一张嘲笑的脸。拉伯雷,他代表了游离于希腊风格的古代戏剧的一张生动面具,有着铜制的肉身,像人一样生动的面孔,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嘲笑着我……”雨果甚至将莫里哀与拉伯雷加以对照,“在莫里哀那里只看到猴子,拉伯雷这里却看到半兽神”。
伴随着言谈的是声音,《应物兄》是李洱以前众多小说的回响和延续,而我们需要的是倾听,倾听那一直播放的《苏丽河》,那九曲黄河的涛声,一阵又一阵;那无数诗词的吟诵,不绝于耳。还有那双林院士和乔木先生一见面就抬杠,仿佛是永不休止的争执声,虽然小说最后以浓墨重彩写出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共同情感,但争执之声真的消解了吗?抬杠和争执是永恒的对话,《应物兄》中充斥着对话,小说中更多的人物虽没有当面抬杠,但内心之间始终是争执的。代际的冲突不可避免,就是和谐大师程先生与儿子之间的冲突亦不可避免,那是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责任赋予文化史以意义。对卡冈和巴赫金来说,人类的不朽与其说在于遗传和生物体上的代代相续,与其说在于假定的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不如说在于当代融入文化史中去:对话一旦终结,人类也就不复存在。想想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分歧,巴赫金参与其中,终其一生,从未停息。
李洱的小说告诫我们,不要把思想错当现实,也不要把现实错当思想;不要把学识错当见识,更不要把书本误认为行动;既要有对理性的忠诚,也不能缺乏对非理性的迷恋。既然小说具有社会性,那么它也具有认识论的特征。这种艺术形式恰好诞生于人类恒定的现实感消亡之时。读李洱的小说,警钟长鸣的应是“虚构”一词,虚构是人类得以扩展自身的创造物,一种能从不同角度研究的状态。作者往镜子里看,却只能看到写作的东西。这是一种隐喻,它似乎要打消写作想要描绘成或反映出不是它本身的那种东西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装上索隐和考据的翅膀,也无法越过虚构的重围。与此同时,又要对隐喻的狡猾声音保持高度的警觉,如果我们从迷宫的人口处,被解开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离谱将离我们不远了。
动机在大量对话中起作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一定起作用。动机依赖于听众对我们表示赞同的程度,即对人的一般特征的赞同程度,或依据一些相同的感受。动机看起来依赖于我们的情感或情绪,但情感和情绪就其表面来说无法得到证明,明亮眼睛和锃亮外套的行为学意义是不一样的。在道德之境中,我们究竟看到的是圣人还是妖魔。儒家的道德秩序、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或斯多葛派的顺从天命,加上现代化的步伐和资本的期望值能否在“烧头香”中彼此兼容,还真是个问题。梦想过上令人尊敬的生活,在现实中却喜欢隐藏或否认自己的弱点。道德环境和道义说教彼此混杂,哲学家即使在思考伦理道德的时候,也不能摆脱伦理环境的影响。在凭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场景时的所言所思,在回顾已逝去二十年的文德能的精神遗产时的所想所记,在企图复活那过去的客厅议论和那具有象征意义的小饭店和旧书店时,不知乔木先生们做何反应,还有那远在海外的程先生们有没有感觉,更不用问的是几十年后陆续登上舞台的“70后”“80后”“90后”了。
修辞没有理性的“启蒙”色彩,启蒙着重类比、联系、统一和复制,而修辞对应的是毁坏、颠倒、歧义或者歪曲。它们被用在时间(机会)和特定场所(面具)中,体现他者和他者的关系。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文学作品成了一面“镜子”,它记录了历史的机缘巧合,以“扭曲”的方式表现特定的社会或语言系统。文德能的过早离世既是个人具体命运的真实故事,同时也是个隐喻,是一次反讽式的戏仿,它隐含着对一代学人过早夭折的无限感慨。文德能阅读中的芥川龙之介,并非我想象中的芥川龙之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