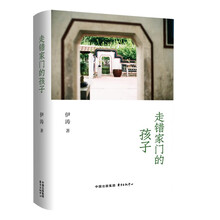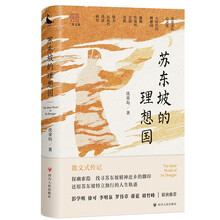20世纪40年代,西洋美术对中国绘画产生了一定影响。伍蠡甫意识到,今后中外文化关系日益密切,研究任何中国文化形态,都须从这一关系上去找答案。国画家也可以从西洋各种画风探求国画的新形式。针对当时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影响,他提醒道,“国画对于这超现实主义之撇开形象,徒事科学的游戏,实有戒备的必要。因为使艺术受科学的洗礼,是一件事,使艺术等同于科学,而否定自身,却又是一件事。国画者为了避免这不必要的混同而灭绝了艺术,首应保持其传统尊线的态度,认清线是形象的提炼,而不是形象的符号与标记,甚或形象的消灭。他应当明白,以线存形原属艺术创造的基本手段,尊线不是‘落伍’,而是强调这一手段。……东西文化接触日密,国画中具此根本作用的线条,今后将对世界绘画艺术的发展有所贡献”。②
1942年,伍蠡甫在拜读了英国艺术批评家赫伯特·里德的最新几部著作之后,有感于里德先生与自己都很重视“形式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作用”的共同见解,伍蠡甫曾向里德先生致信。他在陈述了关于超现实主义绘画脱离形式的见解之外,向里德先生介绍了中国绘画艺术在巧妙糅合自然与自我,实现“物我融合”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和美学特质:(中国)艺术的修养工夫,要做到忘了物我,然后物我始而彼此接近终乃彼此圆融,不可强分。若更从艺术以外说,这不可强分确自有其远大的作用,可使人有“己”也必有“他”,有“人”也必有“我”,“彼此”“此”互通,浑为一体。这个作用,倘能善为发挥,更可以养成为己即是为人、为人即是为己的信念与作用,使人格扩大而且深化,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当有裨益。艺术至此,也不复仅是画斋、客厅里面的装饰品了。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的绘画乍看好像不切实际,然而它的优良的传统,却是质朴而且并未顷刻忘记了人生。
他深信中国绘画艺术传达出的“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精神能够为世界“明日的艺术”提供经验与智慧。伍蠡甫对线条的本质及其艺术功能与审美价值的研究,深入推进了中国绘画美学研究,并赋予其更大的学术生命力。
新文化运动以来,研究中国画论的著作大致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针对当时从事中国画论的研究群体,伍蠡甫分析指出国内的作者大都同时也是画家,懂得中国绘画传统的旨趣和技巧。但随着西洋艺术影响日深,原有的画论研究者未必能够准确把握处在创新嬗变中的中国绘画。“加以国画家大都墨守成法,不很愿意兼通艺术的一般理论,对于和艺术密切相关的其他科学,也不感兴趣,于是他的著作,在纵的方面,不易捉取过去国画发展的原则,在横的方面也就无法理解各种不同作风、派别、方法等所共具的和独特的意义了。换言之,我们近来的国画研究者,似乎太过囿于历代权威的意见,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些意见的零星的重述,抑即就材料的累积,不能使读者从中看出什么系统的解释。他们又喜欢博引过去习用的抽象的字面和批评的滥调……而不能进一步予以比较科学的说明,又或刻板似地写上许多类乎神话的诸大名家的遗闻轶事,而不肯说破它们的荒谬无稽,凡此更给读者添了不少的困难。因此,我们所有的关于国画的论著,在大体上可以说是失败了。”①针对国外学者对中国画论的研究,他认为就他所看过的专著而言,它们在方法、取材与综合的见解上,都比国内著作稍胜。但是由于国外学者大多鲜有亲自进行书画创作的体验,因此对国画创作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仍存有隔膜和陌生感。另外,由于有些学者无法识别画迹的真伪,致使他们的著作中所选印的代表作品的图片,其原迹多半是赝品,因此更加影响他们对中国画艺术进行正确的考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