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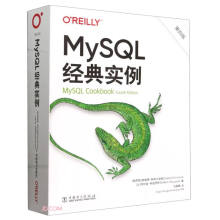
1981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
以上千页的篇幅展现彼得大帝厚重的一生。
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波澜起伏的情节勾画俄罗斯帝国的兴起
自从回莫斯科起,彼得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些正在沃罗涅日建造的船只。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的拷问仍在继续,尽管彼得和他的朋友正在用酒精来打发秋冬时节的阴郁长夜,沙皇仍恨不能立刻前往顿河,同他招募的西方船匠会合,这些船匠此时甚至已经开始在河岸的造船厂内工作了。
10月末,他首次造访顿河。许多波雅尔渴望让自己恩宠不衰,为此他们与沙皇形影不离,并跟随彼得一道南下。公爵切尔卡斯基——这位德高望重、得以留须的长者,此时以莫斯科地方长官的身份留守后方,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非大权独揽。彼得的特点是绝不会把政府托付给一个人,而是同时交到几个人的手上。在动身前,他也对戈登说过一句话:“我将一切都交托予你了。”他还对罗莫达诺夫斯基说:“现在,我把一切事务都托付给你那颗忠诚之心。”1 彼得组建摄政府的准则是将权力分交给多人,让每个人都搞不清自己手中究竟掌握着多大的权力,这样他们就会陷入持续的对立和困惑中。这一体系不太可能在他不在朝时提高政府的效率,但可以阻止某个摄政者挑战皇帝权威的现象再度发生。由于射击军叛乱的起因仍未确定,建立分权体系成了彼得首先要考虑的事。
在沃罗涅日,一座座造船厂沿着宽而浅的河岸不规则地排列开来。彼得看到木工们正在又锯又锤,随后,他发现了很多问题:人手极度短缺、船材浪费严重,船匠们急于执行沙皇的命令,用的是未经干燥处理的木料,这种木材一旦入水就会迅速腐烂。 从荷兰赶到后,克勒伊斯中将将船只检查了一番,而后下令将大批船只拖出重造、加固。没有来自上级的指导与约束,每名外籍船匠都只遵循自己的设计方案,因而争吵频频。按照彼得从伦敦发来的指令,荷兰船匠必须在别国船匠的监督下工作,他们愠怒不已,消极怠工。俄国工匠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群奉命至沃罗涅日学习造船技术的人心里清楚,一旦他们展现自身资质,就将被送往西方深造。因此,许多人宁愿对工作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希望借此获准返乡。
最严重的问题存在于大批未经训练的劳工中,这群人遭受的苦难也最为深重。数以千计的农民和农奴受到征召,他们从未见过比驳船更大的船只,也从未见过比小河更宽敞的水体。他们带着自家的斧头——有些人还牵来了自家的马匹——将树木伐倒,砍去树枝,然后让它们顺河而下,漂往沃罗涅日。他们的生活环境极为简陋,疾病得以迅速传播,死人是常有的事。逃亡者众多,最后造船厂不得不筑起围墙,设置岗哨。逃亡者一旦被抓到,就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丢回到工作岗位上。
尽管彼得表面上持乐观态度,但工程进展缓慢,工人成批病倒、死亡、逃亡,这些都让他忧心忡忡,沮丧不已。1698年11月2日,来到沃罗涅日3天后,他写信给维尼乌斯:“感谢上帝,我们的舰队状况良好。如今只有一件事让我放心不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体验一下这些成果?它们就像枣子一样:种下它们的人还从未成功收获过呢。”2 其后,他又写道:“托上帝的帮助,准备工作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但我们只能等待幸运日的到来,到那时,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浓重疑云或许就会散去。我们已经开始动手建造一艘预定装备60门火炮的船了。”3
虽然彼得忧心忡忡,但造船工程仍在进行,尽管造船厂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一切工作都要靠手工工具来完成。一队队工人和马匹搬运着一根根树干,将它们砍削成圆木,而后拖过围场,运至位于土坑之上的存放位置。然后,一些工人下到土坑里,另一些人则倚靠或是坐在圆木上,好把它固定住。长长的船壳板和弧形的肋骨板材则是通过锯与凿的办法制成的。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因为一根圆木可提供的板材少之又少。一得到毛坯板,它就被转交给更为熟练的工匠,后者用短柄斧、锤子、大槌、螺丝钻和凿子将木板塑造成所需要的形状。最重、最坚固的板材被制成龙骨,离地放置。随后,肋材被弯曲,直到可以固定在一起为止。最后,那些沉重的木板被沿着船帮组合起来,以防止海水渗入船体。然后就可以开始甲板、内舱及所有特殊结构的制造工作了,它们将把这条船变成一座居所和一台作业机器。
整个冬天,彼得无视严寒,与手下一起埋头苦干。他走过一座座造船厂、跨过一根根被积雪覆盖的圆木、走过一艘艘静静屹立在船台上的船只、走过一群群围聚在露天火堆旁试图温暖自己的双手和身躯的工人身畔、走过一间间铸造车间——在那里,一台台巨型风箱将空气挤进正在铸造船锚和金属配件的火炉内。他又是下令,又是劝诱,又是说服,不知疲倦地倾泻着自己的精力。负责制造桨帆船的威尼斯人抱怨工作太过辛苦,以至于他们都没时间做告解了,但舰队的规模依旧在扩大。当秋季到来时,彼得发现已有20艘船下水,泊于河内。随着冬季时光一天天过去,每周都有五六艘船下水,或是在船台上等待着准备在冰雪消融的时候下水。
彼得并未满足于全方位监督,他亲手设计并开始建造一艘拥有几十门炮、名为“宿命”号(Predestination)的船,这艘战舰完全由俄国工人负责制造。他亲手安装龙骨,并与陪在自己身边的波雅尔一道将它固定住。“宿命”号是一艘漂亮的三桅船,长130英尺。制造它的过程中,彼得体验到了工具在手的愉快感觉。他知道,终将有一艘出自自己之手的战舰要在黑海海面上乘风破浪,因此越发愉快。
在彼得第二次造访沃罗涅日期间(3月),弗朗西斯·勒福尔去世了,这对沙皇本人而言是一记令他头晕目眩的打击。彼得两次于冬季跑去完成自己的造船事业时,勒福尔都留守莫斯科。时年43岁的他似乎依旧精力旺盛,满心热情。身为大特使团的特命全权大使,在西方的18个月间,他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庆典宴会的考验。回到莫斯科后,在秋冬季节的酒会和喧嚣的招待会期间,他那惊人的酒量也毫不逊色。当他目送彼得前往沃罗涅日时,似乎依旧满面春风,情绪高昂。
但在去世前的那段日子里,勒福尔尽管仍在继续自己的疯狂生活,一个诡异的故事却开始传扬。一天晚上,他妻子听到丈夫的卧室内传来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当时勒福尔并不在家,而是睡在另一个女人的床上。勒福尔的妻子知道勒福尔不在家,但她“猜想丈夫可能已经改变了心意,怀着怒不可遏的心情回到了家。于是她派人去查明原因。那人回报说,自己在房间内没有看到半个人影”。4 即便如此,响声仍未消失。根据勒福尔之妻的叙述——这个故事是科布讲述的,“第二天一早,全家的椅子、桌子和座椅被丢得到处都是,四下里一片狼藉。此外,沉重的叹息声彻夜清晰可闻”。
不久之后,勒福尔设宴款待两位别国外交官——丹麦大使和勃兰登堡大使。两人受彼得之邀,即将前往沃罗涅日。当晚的宴会很成功,大使们一直待到很晚。最后,房间里的温度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主人领着客人,步履蹒跚地来到户外。在冬日的冰冷空气中,他们既没穿外套也没披围巾,头顶星空,举杯畅饮。第二天,勒福尔开始浑身打战。热病症状迅速加剧,他陷入精神错乱,开始胡言乱语,叫嚷着索取音乐和酒。浑身哆嗦的妻子建议派人去请新教牧师施通普夫(Stumpf),但勒福尔咆哮起来,说他不想让任何人靠近自己。施通普夫还是来了。科布写道:
当牧师获准前去看望他,并劝他皈依上帝时,他们说他只是告诉牧师“别多费唇舌”。他妻子在他弥留之际,请求丈夫原谅她的一切前愆,要是她犯过的话,他和蔼地答道:“我从未有什么要责怪你的,我一直尊敬你、爱你。”……他把他的仆人和他们的服务夸奖了一通,并请求全额支付他们的工资。5
勒福尔又活了一个星期,临终时,有人请来一支管弦乐队为他表演,音乐给他带来了慰藉。最终,他于凌晨3点去世。戈洛温立刻给勒福尔的住宅贴上了封条,并将钥匙交给他的亲属。与此同时,他急急忙忙地打发一名信使前往沃罗涅日的彼得处。
当彼得听到这个消息时,手中紧握的短柄斧落了下来,他坐到一根圆木上,以手掩面,泪水滚滚而下。一阵嘶哑的啜泣和悲叹过后,彼得说:“如今我是孤身一人了,再也没有一个可值得信赖的人。他是唯一一个忠实于我的人。现在我还能信任谁?”6
沙皇当即返回莫斯科。葬礼于3月21日举行,彼得亲自安排殡葬事宜:这个瑞士人将享受国葬待遇,其规格之宏大,全俄国除沙皇或牧首以外无人能及。外国大使被邀请出席,波雅尔们则被勒令出席。给他们的指示是:早晨八点在勒福尔宅集合,将遗体运往教堂。但很多人迟到了,再加上其他因素的耽搁,游行队伍直到中午才算集结完毕。与此同时,彼得按照西式习俗,已在屋内为宾客备下了一顿丰盛的冷餐。波雅尔们对出现在面前的宴席惊喜不已,立刻扑了上去。
科布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餐桌被摆开,珍馐美味把它们压得“嘎吱嘎吱”作响,酒杯排成长列,碗内盛着各式各样的酒。加香料的热红酒被供给喜好它的人们。俄国人—不分出身贵贱、官职大小,均不得不奉沙皇之命出席葬礼,他们坐在桌边,大口大口地吞食着冷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鱼、奶酪、黄油、鱼子酱等。
波雅尔舍列梅捷夫游历甚广,作风文雅,穿衣打扮为德意志风格,胸前挂着一个马耳他十字架。他认为与其他人一道狼吞虎咽有损自己的尊严。沙皇开始频显悲态。哀伤的表情在他脸上挥之不去。大使们恰到好处地献上殷勤,按照西式风俗向沙皇深深鞠躬,皇上则优雅地答礼。列夫·纳雷什金急不可待地离席去见沙皇,他实实在在地向陛下表达了自己的亲切致意,后者却依旧茫然若失,竟一时没有答复,直到回过神来,方才躬身与纳雷什金拥抱。当运送灵柩的时刻到来后,悲伤和旧情一下涌上沙皇和其他一些人的心头,众人对此洞若观火,因为沙皇是所有人中流泪最多的一个。在聚集于现场的众多人士的一致注视下,沙皇给了死者最后一吻。
…… 遗体就这样被带往归正会教堂,在那里,施通普夫牧师做了次简短的布道。离开寺院时,波雅尔和其他俄国人把游行秩序弄得一团糟,他们本着愚蠢、自负的作风,将别人推到一边,强行挤到灵柩处。外国大使佯装没有看到这傲慢的一幕,俄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挤到他们前头,就连那些(根本没有资格这样做的)卑贱之辈也是如此,大使们却默默忍受着。当他们前往墓地的时候,沙皇注意到队列顺序起了变化:他的臣民先前跟在大使后头,如今却排到他们前面去了。于是他唤来小勒福尔(弗朗西斯·勒福尔的侄儿),问道:“是谁打乱了队列顺序?为什么那些本来跟在后面的人这会儿跑到最前头去了?”勒福尔依旧拜伏在地,没有回答,沙皇命他开口。当小勒福尔表示,是那些俄国人粗暴地把次序颠倒了过来时,沙皇勃然大怒:“他们是一群狗,不是我的波雅尔。”
舍列梅捷夫的表现截然不同——这或许要归功于他的审慎,仍与大使们走在一起,尽管其他俄国人都已经挤到前头去了。火炮在墓地和公路上排列成队,三波火力后,连空气都在颤抖。各团的火枪手们也来了一次三轮齐射。一个炮兵在炮口前傻站着,结果脑袋被炮弹扯飞。沙皇率军返回勒福尔宅,众人一齐跟在后面。每个前来参加丧礼的人都得到了一枚金戒指,上面刻着死者的逝世日期和头像。沙皇稍微出去了一下,波雅尔们就一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家里赶。当他们走下几层台阶时,与归来的沙皇来了个面对面,波雅尔们又退回到房间内。波雅尔们急于离开,这让沙皇起了疑心,以为勒福尔的死令他们欢天喜地,心中的火腾地一下蹿了起来。一怒之下,彼得对他们吼道:“呵!他的死对你们来说是一件乐事,对吧!他的死对你们来说是一大胜利,对吧!为什么你们全都不肯等会儿再走?我看你们是太开心了,所以已经无法强撑着做样子,也没法再装出一副悲痛的表情了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