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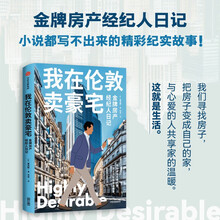






在20世纪早期的畅销书《舆论》(Public Opinion)中,美国作家、政治评论家沃尔特 ·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真实的外部环境过于庞大、复杂、变化无常,以致我们很难直接获得全部真相。”现代人希望为社会所用,表现得见多识广,退避到一种选择性的真实—“拟态环境”,即一种对世界主观且有失偏颇的简单解读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与强调,塑造了我们与所处世界—自我创造的“象征性现实”之间的互动方式。
与中国35年的交往,帮我形成了关于中国“拟态环境”的个人理解,尽管我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误解是正常和良性互动的表现,也促使我不断调整对中国的认识。
然而,在中西方互动的关键节点,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却正日趋僵化。选择性报道和道貌岸然的傲慢塑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而我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种声音。
的确,我在这里受到的尊重和热情款待影响了我对中国的感受,但我的观点并非来自“信息孤岛”。我曾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旅行和工作,最终选择了中国作为我的家。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儒家文化使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受到相应的尊重,这种尊重有时甚至超过了我们在美国的身份地位。中国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名人,我们中很多人利用这种受之有愧的认可来定义中国,他们甚至从未离开过北京或上海的西方人舒适区。
抱着对既有价值观的道德优越感来到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拒绝了学习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难得机遇。西方世界对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非常自信,以致难以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挑
战,尤其是价值观有时与西方不甚匹配的国家。我们过于注重差异,特别是消极层面,却对中西方无数相似之处视而不见。我们无法就所有个体应如何生活得出一个统一答案。我对中国的预言经常被证明是错的,这让我保持谦卑。然而,这些误解并没有使我远离中国,反而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究我们彼此之间的分歧。
以赛亚 · 柏林在短篇小说《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阐述了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思想:“狐狸广博,但刺猬精深。”柏林认为,狐狸对多元观念持开放态度,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采用不同的答案。刺猬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思想家,就像古希腊的一元论者,坚持一种独特的视野。
我比较认同狐狸。尽管柏林后来开玩笑说,他从来没打算认真对待他的二分法。但我相信,仅凭一句格言,一种对世界的单一看法,无法获得人类经验和价值观的多样性。这句话在探讨未来中国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时最为适用。
当全世界都在批评我的第二故乡时,中国街头治安稳定,医疗费用可以承受,乡邻把孩子们送进有政府补贴的大学读书,乐观主义无处不在。政府主导的国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包括世界应用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网,这激励着我们所有人。我的乡村伙伴们经济状况不断改善,生活日益富裕,还有20年前难以想象的政治和知识上的开放。
中文“自由”一词认为,个体自由与他/ 她的理性或更大的整体目标相关,换句话说,与整个社会相关。这种自由从集体视角出发,并未脱离社会存在的具体现实。中国文化崇尚家庭、尊重长辈、重视教育,中国人从这些关系中获得象征性的价值和目标。在中国,个体特征与共同的社会操守密不可分。
中文中的“自私”一词,与“自由”的第一个字都是“自我”的“自”字,并且第二个字“私”也表示“自我”。其含义显而易见—过多的自我。我们西方人在追求个人主义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更大的整体。我们赞扬思想的多样性,却不愿接受相反的观点。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每个个体的生存都取决于其身处的社会结构。
中国和西方都渴望社会和谐。但是,西方在歌颂个人主义的同时,淡化了对社会整体的关注。中国也重视自由和个人价值,但并不以牺牲社会团结为代价。中西方用同样的色彩来描绘社会图景,但我们却强调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西方过于强调言论或行动的自由,而非犯罪、贫困或负担得起医疗保健的自由。在亚洲,人们通过理解自身与他人的关系来认识自己。在我看来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却很少有亚洲以外的国家愿意尝试理解和欣赏这些差异。
我不能从一个单一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价值观并非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在特定时期创造的共同体和文化。中国有5 000 多年具有开创性的价值观,如果西方像刺猬一样过于自信和固执地批判这些传统,则注定会在外交上失败。
那些以刺猬视角看待中国的人,无法完全理解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巨大勇气。我认同这种勇气,它帮助我在竞技场上公平竞争。相比我在斯坦福的同学,我觉得中国人更有亲和力。早年与那些同学的交往并没有将我同化,反而让我更加珍惜自己自力更生的价值观。如果西方继续呼吁中国改变,中国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在两者之间看到了相似之处。
19 世纪末,鲁德亚德 ·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赞扬了美国向亚洲的扩张,称美国有责任照亮世界上仍处于黑暗中的各个角落。他在《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宣称,教育和改造非白人国家是西方文明的道德与责任。
在过去的35 年里,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如何建立起它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实力地位。吉卜林笔下的“白人的负担”精神,在今天仍然和他那个时代一样令人迷惑。西方世界应该正视
中国的存在,而不是按照西方的臆想与中国互动。可能中西方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是不断试图劝服对方可能永远无法彻底解决中美两国的世界观差异。
最终,我们只有认识到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挑战时,才能开始超越我们的“拟态环境”,理解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必要性。让我们以开放和务实的态度来应对这些分歧,做一只开放包容的狐狸,而非一只固执短视的刺猬,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交往才能走得更远。
序
一尊面恶心善的守护神
种子
01 勇气与希望
大理的约拿
02为什么是中国?
包容的南诏古国
03通往中国的漫漫长路
一尊悲悯的观音
落地
04新语言
马可·波罗与中国穆斯林探险家
05中国式电影制作
过桥米线
06我的第一次被捕经历和崇高的体验
明朝历史上的冒险家
07医生的爱情时代与飞鸽时代
民家或白族:大理人
08北京街头的日常与历险
吉祥的开端
生根
09南京的魅力
杨品相宅的成形
10失去的身份
11世界越来越小
约瑟夫·洛克和植物入侵者
扎根
12从事新职业
13寻找大理
焦土之地,空中飞虎
14喜林苑的开幕
15村官与乡绅
16农业技术变革对喜洲的影响
生长
17居家教育
天堂通勤颂
18旅程的经验教训及对未来的期许
19破碎的天神与新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