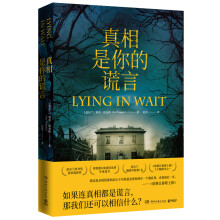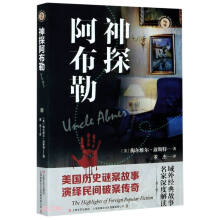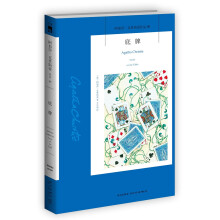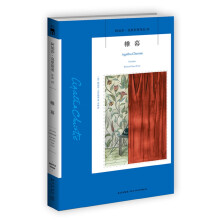从洛阳到南阳一路坦途,沿路山川平顺、田园秀美,本是天下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然而近年连遭蝗灾洪水,荒芜之迹,若隐若现,鲍德与张衡见此光景,皆摇头叹惋。昔年世祖光武皇帝起兵于南阳春陵,征战四方,定都洛阳,两城之间短短四百余里,他整整走了一十二年。如今鲍、张一行,赴任心切,轻车快马,不出十日,已抵达南阳城下。
自十六岁外出游学,转瞬之间已过去了七个春秋,张衡早已脱去了昔日青葱少年的影子,成为了英姿勃发的学者与初当重任的官员。七年之间,虽然鸿雁往来,音讯频繁,但张衡对家人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回到南阳,他向鲍德秉明,先去家中看望母亲,再到公府赴任。母亲闻知张衡要从洛阳归来,打十余日前,便每日派家人前去城门观望,今日见鲍太守的车马入城,母亲早早在门前迎接,母子阔别重逢,相对垂泪,总有说不完的话。
听母亲讲起,近几年年景不佳,南阳街市萧条了不少,唯鲜衣怒马的豪族子弟仍然悠游恣肆,甚至较往年愈加跋扈了。灾害让不少农人流离失所,变为所谓的“流民”,既令人生怜,也不由忧虑他们会渐渐沦为盗寇,为祸一方。母亲口中的情况令张衡忧心忡忡,在他的记忆里,南阳还是一座弥漫了童年绮丽梦想的城市,无忧无虑的家乡,但如今,自己是肩负重担回来的。
“衡儿啊,你便大着胆子做事。”张衡的心思又怎能瞒过母亲呢?“天命会给你回报的。”
“母亲啊,你可不知,儿子在洛阳,正是因为不信天命而出名哦!”张衡心中苦笑,但这话却是不能讲出口的。
张衡担任的是南阳郡的主簿官,平日的任务是典理文书、掌管档案,乍看起来清闲,实际却是太守鲍德重要的参谋。到任后的两个多月间,鲍德在张衡的辅弼下仔细地阅览了历任南阳太守留下的文书档案,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他已渐渐了若指掌。鲍德的勤勉让张衡十分欣喜,他逐渐确认,对眼前这位大人,自己可以彻底地敞开心扉。
“平子以为,南阳之弊何在?”这一日,正在翻阅文书的鲍德突然问起。
“在豪族。”张衡答得干脆。
鲍德默默不言。南阳是光武皇帝的故乡,功臣家族云集,与洛阳长安儒学传家的情况不同,这些家族子弟大多仰赖祖上军功,不肯勤勉向学,其中一些更是游手好闲,为害乡里。历任太守意欲扭转风气,奈何势单力薄,皆难以成功,张衡上来指出的便是一块硬骨头,然而,他的神色间却泰然似有自信。
“那如何应对呢?”鲍德好奇地问道。
“南阳官学废弛已久,教化不兴,民风怎能淳厚?在下以为,官学不但要重建,还要建得更加阔大,广收学徒,恢复风雅。”张衡答。
鲍德一怔,问你豪族之事,为何要提到学校?转瞬间,他明白了其中关节。若能将豪族子弟汇集到官学中来,加以约束教化,岂不是治本之法?思及此处,鲍德颔首微笑道:“甚好,甚好!然而此事急不得。”
“为何?”张衡纳罕道。
“自永元七年起,京师地震,天下水、旱、蝗灾频发,南阳虽富庶,又怎经得起连年赈灾?左支右绌,又如何使钱去兴办官学?”鲍德解释道。
“在下思虑不周,望使君恕罪。”
“平子何罪之有?这兴学的事,日后还要交给你来办哩。”
很快,南阳郡府上下都发现,太守鲍德越来越忙碌。他不是行走在乡野之间检视田地,便是亲赴险峻勘察山川,而与他同行的,总有主簿张衡。
“天灾的种类很多,但祸害农事最大的,莫过于水、旱、蝗。”这日,鲍德带着张衡与一众随从勘察清水。淯水自北向南穿过南阳,汇入汉水,南阳之水患,多在此河。“治水、旱,皆需要早做工夫,筑堤防,修渠道,掘水源。此时耗资虽巨,总好过日后赈济。”鲍德道,“天灾,天灾,说是上天之事,其实亦不尽然。修明治道,天与佳年,固然是最好的,然我等守土一方,总不能全赖在缥缈之事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