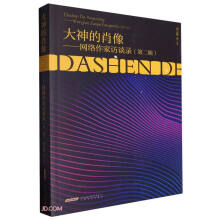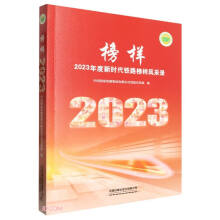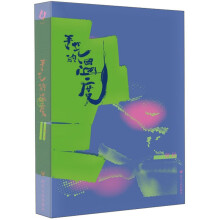忆雨洲校长
雨洲校长是我敬爱的恩师,又是与我们家交往较密的亲戚,我常常和他接触,因而受他的教诲和影响特别多。在我人生的旅程中,无论是在益群中学和昆明求学的学生时代,还是在参加工作之后,都得到他很多教育、帮助和关怀,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现略述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
我从高小到进入初一,都是一名学习上不刻苦、功课成绩平庸、贪玩爱闹的孩子。夜间往往因贪看小说而搞到深夜,早上又起不来,母亲曾将我的这些“德行”对校长讲过多次,要求他对我要特别严加管教,因而校长也就对我特别严厉。
1940年,我13岁,年长的许锡年同学结婚,我去“吃酒”,客厅里摆着待客的草烟、旱烟,出于好玩,我也仿效大人们抓一撮来卷着想学抽。当我正低头卷烟时,突然一只大手把我的烟一把抓去,猛抬头一看,是校长,把我吓得不知所措而低下头来,只听他训斥道:“这么大娃娃就要抽烟,太不像话,再长几岁就要抽鸦片烟哕!”我又害怕又害羞,只顾低着头摆弄衣角。接着又听见他和蔼地说:“你已经是中学生了。抽烟对不对,你自己去好好想想看。”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学抽炯了。
1941年至1942年,我们益群中学二班英文教师是郑汝骊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主任),他博学多才,教风严谨,很受同学爱戴。我们每天早晨第一节课都是英文课。上课开始时,师生用英语互道“早安”后,郑老师都要抽查几名同学站起来背诵一段或几段英语。我和几个个子小的同学坐在第—排。我的座位就在讲桌下面,郑老师往往把头一低就盯住我并喊我站起来背诵。有时虽然连喊几人都没有喊到我,但最后郑老师还是把头一低又盯住我,喊我站起来背诵。由于经常这样,当喊到我的名字时,同学们都忍不住笑。我对此总感到“委屈”。心想:我从来没有一次背不得,为什么总是“幽着”(云南方言:盯着不放的意思)我?恐怕是因为我座位在老师眼皮下面,总想调换个座位。哪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校长叫郑老师这位英文老师对我要特别严格,不能放松。正由于对我的严格,迫使我不得不天天熟读英语,从而养成了我一直到进大学后都有天天读或背英语的习惯与能力,大大促进我的英语学习,我的英语基础扎实,后来能译“大部头”。
1942年5月,家乡被日寇侵占前夕,由于缅甸战局急转直下,旅缅的和顺乡同胞纷纷返乡。每天傍晚,一批批从缅甸撤退的远征军伤兵络绎不绝地从上庄顺大盈江往大西练方向走去。整个腾冲人心惶惶,一片混乱。5月8日早上,我又因贪看小说到凌晨2点左右才人睡而起迟了,脸也顾不上洗,抓起书包就往学校跑,到尹家巷遇到寸守恕同学从对面跑来,他说今天早上没有上课,校长叫他跑去女生部(尹家宗堂)喊女生,要马上全部到礼堂集合。我生怕上课迟到,听说不上课就放下心来,不再跑了。到达礼堂时,同学们(男生)都已集合了。我赶紧钻进人群,插入队列,站好一看,校长和老师们都不在,同学们却静静地站着,平时那种互相嬉戏的场面都没有了。我感到有点奇怪,却猜不透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和益群中学女中的女同学都来了。站齐后,校长和老师们从教员体息室来到礼堂,校长走到孙中山总理遗像前开始讲话,他的脸阴沉着,神色和平时大不一样,他的声调低沉而凄楚,虽然我站队的位置因个头儿小而在最前排,但校长的声音有时小得连我听着都感到有点吃力。他缓慢悲沉地说:“同学们!昨晚县里得到自龙陵跑来送信的消息说,敌军已经侵占龙陵了。看情况腾冲也马上就要沦陷,我们经过慎重研究,不得不决定学校……从今天起……停课……”讲到这里校长的喉咙哽住了,悲痛得说不下去了。
听到这突然的宣布,我仿佛头顶上被雷轰了一下,眼前的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老师们严峻而愁苦的神色,同学们惊疑得发呆的面孔,让我无所适从,我感到茫然,迷迷糊糊地又听见校长说:“……你们都曾经读过《最后一课》(法国都德的小说)。今天……也就是……是我们的最……最后一课了……”校长的声调越来越凄切。左边的女同学有人用手帕偷偷擦眼睛,隐隐传来轻微的啜泣声……
“……有的同学平时不好好用功读书,从今天以后,你们要想再读,也就……在日本军侵占的地区,他们都要我们中国人做他们的顺民,受他们的奴役,每一个黄帝的子孙都不甘愿当‘顺民’做亡国奴,我就是不愿做‘顺民’才从北平跑到后方来,想不到现在又……”校长的话被哽得不成声了。女同学那边的啜泣声由小变大,她们几乎全哭了,男同学这边也有人抽泣起来,校长的眼眶也红了,他掏出手帕,擦擦眼镜,又揩揩充满泪水的眼睛。我失魂落魄,想哭也哭不出来,木然地呆呆站着,最后只听见校长继续说“……我相信你们也不愿当‘顺民’……”往下去我就恍恍惚惚地听不清了。
从此我们亲爱的母校被解散,校长离开了他辛苦耕耘过两年半的园地,逃到大后方。而我们朝夕相处、情同兄弟姊妹的同学们就开始四处逃难。
P2-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