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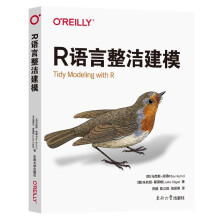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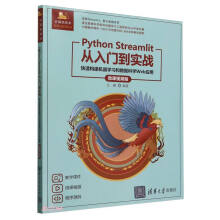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欧洲人不震惊于中国的幅员之辽阔,他们觉得,中国每一个省的面积几乎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由于地理学尚不发达,欧洲人以为中国的领土呈四方形,东南濒临大海,西部边界止于陇西,南部达于海南岛,长城则是中国的北方边界。他们把长城以北地区称作鞑靼,而所谓鞑靼人则包括满族、蒙古人和聚居在中亚细亚的许多民族。欧洲人认为中国得天独厚,除了北方沙漠,东、南、西三面都有天然屏障。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对于中国地理的无知状态,他不但一一列出了中国15个省各自所辖的州、府、县,而且介绍了各地的地形、山川、城市、物产、交通以及名胜古迹等,所以到了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在此后将近200年中,并无实质性的增补或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甚于对欧洲某些地区的了解。
中国有许多大城市,最著名的是北京、南京、广州、泉州、杭州、苏州、西安。作为首都,北京理所当然地得到最多的介绍和描述。北京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皇宫,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宫殿无数,高台玉墀,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不过,欧洲人觉得,由于门窗不使用玻璃,官室内光线不足,相当昏暗;宫殿虽然雄伟庄严,但是缺乏必要的采暖设备,冬季室内温度很低,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往往冷得发抖。北京的街道整齐,商业繁华,但是黄土路面带来许多不便,大队人马经过时,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看不清五步以外的人和物。南京曾是明朝的京城,与北京一样有雄伟的宫殿和宽阔的街道。居民人数也不在北京以下。广州是澳门之外西洋人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杜赫德说广州的体量与巴黎不相上下,但商业更加发达;站在珠江边,能看到来自欧洲各国的商船。杭州和苏州以其妩媚的景致享誉欧洲。杭州的名声主要来自丝绸和西湖,而苏州则因其市内众多的河道而闻名,马可·波罗曾将苏州比作威尼斯,17世纪以后来华的欧洲人大都认同这一评价,而且指出,若就桥梁的数量而言,苏州则在威尼斯之上。西安作为古都,名声不小,但因地处内陆,到过其地的欧洲人不算很多,它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与出土于其近郊的“大秦景教流行碑”相联系的。到过中国的欧洲人认为,除了这几个城市各有特色外,大多数中国城市是按照一个模式建造的,到过其中一个,便等于到过其余所有城市。
欧洲人对长江和黄河比较熟悉;他们还知道,除了大型河流外,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小江小河,为中国人带来了舟楫之便。对于中国的名山,那时的欧洲人知之甚少,也许因为中国的名山大多与佛教或道教有关,而西洋传教士无论属于哪个教派或修会,都视佛教和道教为传播福音的大敌。
也许由于耶稣会士很少提到中国北方的严寒,许多欧洲人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地处温带,气温适宜,风光秀丽。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在珠江航行时,对两岸的景色做如下的描绘:“两岸绿油油的稻田一望无际,犹如美丽的草场,其间河道纵横,从远处望去,不见河水,唯有小船往来于河上,宛如在草毯上滑行。远处小山顶上绿树成荫,山谷芳草鲜美,就像是巴黎的土伊勒里花园。”在这如诗如画的土地上,盛产稻米和各种蔬菜水果以及鱼虾,所以一些欧洲人觉得中国得天独厚,凡是欧洲有的东西,中国无一匮乏。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歇为此喟然感叹,不明白上帝为何把天堂安排在这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度里。
某些欧洲人曾经认为中国是埃及的殖民地,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法国学者德梅朗早在1734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得到法国汉学家德经和英国的伦敦科学院两位学者的支持。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较多发言权的在华耶稣会士,1763年受到伦敦科学院的咨询,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给予否定的回答。
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外貌,主要来自游记中的文字描述和各种艺术品中的图像。男人圆脸小嘴,蓄八字小胡,戴着形似灯罩的帽子,女人穿着肥大的绣花袍子;无论男女老少,总是佝偻着身子,似乎永远直不起腰来。到了18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发现。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与实际不符。一位游记作者写道:“从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所见到的人物画推断中国人的长相,肯定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事实上,他们既非那样丑,也不那样滑稽可笑。”在陡峭的山崖上,在曲折的小河边,人们在小巧的亭子里饮茶,谈天,听松涛,临晓风,望彩云明月;阳春三月在绿草如茵的田野上放风筝,在柳树成荫的河边垂钓——这就是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