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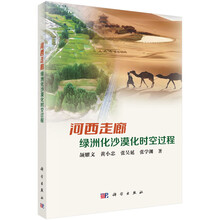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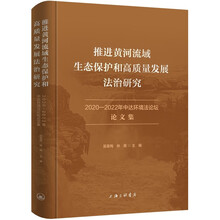

第1章绪论
1.1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反思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等问题相继出现,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人类福祉,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共同议题。可持续发展理念最早可追溯到1972年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后经《21世纪议程》《联合国千年宣言》《我们希望的未来》等联合国会议文件不断发展完善。在2015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近200个国家共同签署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和169项子目标,系统规划了未来15年人类社会的发展蓝图,为世界各国发展和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薛澜和翁凌飞,2017)。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维度,其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考虑环境可持续性(Costanza et al.,2016)。为此,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分别对环境可持续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性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现代生态学之父Odum通过查考生态学(ecology)与经济学(economic)的希腊语词源,认为这两个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之间应具有某些天然的联系(包庆德和张秀芬,2013)。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持对立观点,是因为双方的研究视角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可持续发展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生态环境问题或者经济社会问题,必须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运行进行梳理,进而探寻经济、社会与环境维度间的协调发展之路(彭斯震和孙新章,2015)。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作为连接生态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生态经济学具有弥合分歧、促进融合的重要意义(方恺,2015a)。生态经济学家致力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媒介,搭建研究经济、社会和环境跨维度可持续性问题的桥梁(朱洪革和蒋敏元,2006)。“自然资本”的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1995年,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国家财富核算体系,将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种类型(刘洋和王爱国,2019)。其中,自然资本通过给自然赋予资本的属性,巧妙地将经济学思想与生态学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抓手。
传统经济学视人造资本(包括经济、人力和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效用等同并可互相替代,而生态经济学则认为两类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性质差异:人造资本主要充当将资源流转换为产品流或服务流的媒介(钟方雷等,2008);自然资本不同于一般的人造资本,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要素,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资源的经济价值上,还体现在独有的生态服务价值及存量资本减少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上(蒋萍和刘渊,2012)。Daly(1996)将自然资本定义为能提供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收益和自然资源储藏,主要包括流量资本和存量资本两部分。其中,流量资本维持着年际可再生资源流及其生态服务的供给,在其不足时,存量资本将作为补充而被消耗。自然资本存量不减少是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最低限度,也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特别是生态经济学界的共识(刘颂和戴常文,2021;Pearce et al.,1989;Pezzey,1990;Wackernagel et al.,1997)。
然而,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带来的环境压力已远超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不仅严重威胁地球环境安全,也成为限制人类福祉的重要因素。就我国而言,自然资本约束已经从以技术和经济限制为特征的流量约束转变为以资源短缺甚至耗竭为特征的存量约束。此外,逐年增加的极端环境事件也凸显了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日益减少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谷树忠等,2013)。可以说,作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本已取代人造资本成为人类福祉的限制性因子(Costanza and Daly,1992;Farley and Daly,2006),如何科学、精准地评价自然资本利用状况逐渐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要开展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评估研究。此后,Daily和Ehrlich(1992)对“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研究历程和价值评估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Costanza等(1997)以货币的形式对全球各类自然资本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价值评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1年6月5日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EA)计划,首次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系统进行了大尺度、多层次的监测与研究,提高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的认知(刘洋和王爱国,2019)。继MEA之后,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众多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了自然资本项目(Natural Capital Project,NCP),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本的核算与评价研究,促进了相关成果在实际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总的来说,自然资本的核算方法可以分为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种。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化评估存在较大的局限。首先,相当部分的自然资本还不具有市场,也就意味着缺乏对应的市场价格(Costanzaetal.,2017);其次,市场价格波动,特别是价格下降会掩盖自然资本存量减少的严峻形势(石薇等,2021;Wackernagel et al.,1997);再者,一些自然资本的消耗或退化具有不可逆性,其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难以在短期内被市场充分估计。因此,生物量遥感、物质流分析、能值分析和生态足迹分析等非货币化评估方法成为近年来自然资本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生态足迹方法,尽管存在一些不足甚至缺陷(方恺等,2010;王云平和别雪艳,2009;Giampietro and Saltelli,2014),但不可否认,它为测度人类利用自然资本的状况提供了一条简便、直观的途径,被誉为近年来可持续发展量化领域最为重要的进展(徐中民等,2006)。
生态足迹研究源于20世纪下半叶生态经济学领域的“影子面积”和净初级生产力(NPP)等研究成果(Hartwick,1990;Jasson and Zucchetto,1978;Odum,1975)。在此基础上,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s于1992年正式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并与Wackernagel一道对其理论和方法加以完善(Rees,1992;Wackernagel and Rees,1996)。作为定量评价可持续发展状态的生物物理工具,生态足迹将人类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形象地比喻为负载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巨足踏在地球上的印迹,其新颖的视角备受世界各国关注,被广泛应用于全球(Mancini et al.,2018;Wackernagel et al.,1997)、国家(史丹和王俊杰,2016;Yao et al.,2021)、区域(向秀容等,2016;Chen et al.,2021)、省市(杨屹和加涛,2015;Fang et al.,2018)、社区(孙贺等,2016;Lo-Iacono-Ferreira et al.,2016)、家庭(曹淑艳和谢高地,2016;Song et al.,2015)等各尺度研究,成为当前主要的自然资本核算与可持续性评价的方法之一。
然而,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无法有效区分自然资本的流量与存量,亦未考虑生态赤字在时间维度上的累积效应,不能体现自然资本存量稳定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Niccolucci等(2009)提出了“三维生态足迹”的概念,通过足迹广度和足迹深度两项新指标,对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土地利用所引发的自然资本流量和存量变化进行了初步测度。方恺和李焕承(2012)最早将三维生态足迹研究引入中国,并针对不同地类间生态赤字与生态盈余可相互抵消,进而掩盖自然资本利用真实情况的缺陷,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生态足迹三维模型,用于精准评价地类、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等各尺度的自然资本利用时空特征。这一改进模型已被学术界广泛采纳,成为生态足迹研究的重要方法(杜悦悦等,2016;方恺,2013,2015b;方恺等,2013;方恺和Heijungs,2012;靳相木和柳乾坤,2017;刘超等,2016;吴健生等,2020;张星星和曾辉,2017;郑德凤等,2018;Chen et al.,2020;Wu et al.,2021;Yang and Hu,2018)。
地球作为一个有限的空间载体,如何在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内实现社会经济繁荣越来越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陈先鹏等,2020;诸大建,2019;Rockstr.m et al.,2009)。生态足迹分析方法通过将人类对生物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需求与区域实际的承载能力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判断人类活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Wackernagel and Rees,1996)。但是除生态足迹外,大多数环境足迹(如碳足迹、氮足迹等)仅从消费端考察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压力或影响,缺乏对应的承载力指标(方恺和段铮,2015)。为此,Fang等(2015)提出了基于足迹-边界指标整合的环境可持续性评估(F-BESA)模型,通过将环境足迹与降尺度的行星边界进行比较,定量判断某项人类活动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环境可持续性。F-BESA模型突破了已有环境足迹研究仅考虑压力端的局限性,促进了由环境影响评价向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的范式演进,为科学评价不同时空尺度、不同资源环境要素的可持续状态提供了新的思路(冼超凡等,2019;H.yh.et al.,2016;Laurent and Owsianiak,2017;Li et al.,2019;Wiedmann and Allen,2021)。
当前,有关自然资本利用的研究多集中于自然资本的内涵与核算,鲜有学者将自然资本纳入可持续性评价研究。因此,本书试图回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①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价区域自然资本利用水平?②不同尺度和区域上的自然资本流量占用和存量消耗有何特点?③如何将自然资本研究融入环境可持续性评价?
鉴于此,本书在评述相关领域核心概念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综合借鉴环境管理学、生态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等学科知识,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三维模型提出了新的自然资本利用评价框架,并将其用于城市、省区、国家和全球等不同尺度区域实证分析。在系统总结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行星边界框架,运用整合的F-BESA模型对关键自然资本的全球环境可持续性进行评估与比较。最后,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框架体系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并提出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本利用与环境可持续性评价的研究方向。本书为从整体上判断自然资本利用的环境可持续性、识别关键自然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2自然资本利用的可持续性评价意义
1.2.1完善自然资本核算的方法框架
本书在论述自然资本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生态足迹三维模型的缘起与优势,并围绕存在的问题对模型进行改进和补充,以期较为全面地揭示自然资本流量占用和存量消耗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自然资本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代内与代际公平性,凸显存量资本恒定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性,从而为创新自然资本核算方法提供依据。具体来说,首先,从自然资本的角度明确了生态赤字与生态盈余的性质差异,在此基础上重新推导了足迹深度、足迹广度和生态足迹三项指标在区域尺度上的计算公式,避免了可能存在的低估区域足迹深度、高估区域足迹广度的缺陷,更为客观地刻画了自然资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其次,借鉴气候变化、经济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人均历史累积足迹广度、足迹广度基尼系数和理论足迹广度三项指标,以分别表征人均自然资本占用的历史累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