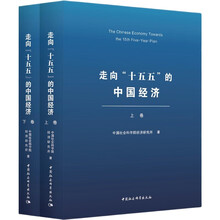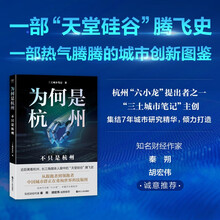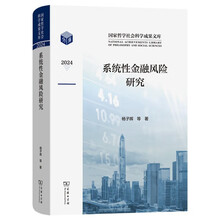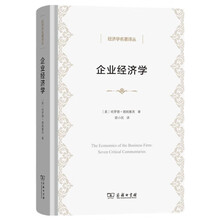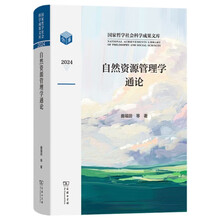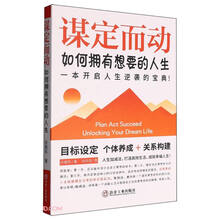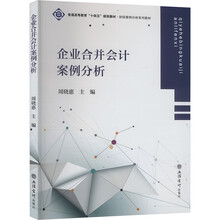第一篇 理论篇
第1章 绿色增长的起源和发展
1.1 绿色增长起源
2005年3月,第五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首次完整地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倡议将绿色增长定义为“强调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进步和增长,用以促进低碳的、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发展”(OECD,2009),绿色增长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绿色增长的发展。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缺乏增长动力的经济急需找到新的增长来源,绿色增长理论的产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必然要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开始反省先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绿色”的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希望在危机远离之后,生产工艺能够得到变革,消费行为能够得到转变。各国政府应对危机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含了“绿色复苏”的目标,这些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成效评价,为绿色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疲软的经济抑制了绿色增长投资的机会成本,给绿色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绿色增长理论逐渐得到认同与发展。各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为绿色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国际社会是倡导绿色增长的主要力量,如OECD、世界银行等组织进行的研究及倡议,不断丰富着绿色增长理论。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指出要“在经济范式改革基础上推进绿色增长”,掀起了国际范围内的绿色增长研究热潮(UNEP,2011)。
1.2 绿色增长形成过程
绿色增长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图1-1所示:环境持续恶化导致了“浅绿色”环保观念的产生;为寻求环境问题的根治途径而产生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思想;由于片面的环境可持续思想举步维艰而进入全面可持续发展阶段;以经济为切入点解决发展问题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发展,绿色增长便是其中的可持续范式。
图1-1 绿色增长的形成过程
1.2.1 环保意识的缺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于1950年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Crafts,1995)。“热增长”使得社会对经济发展抱有强烈的信心,却忽视了资源和环境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种对经济盲目的自信和环保意识的缺乏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普遍推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财富积累,自然无暇顾及经济外部性问题。其次,经济发展尚未对资源需求构成压力,“资源用之不竭”的观念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张二勋和秦耀辰,2002)。*后,在这种非常规性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形成了这个时期的经济理论(Heinberg,2011),经济学家将“增长无限”视作约定俗成的真理。可以说,利己主义价值观和西方经济理论分别在意识形态与思维逻辑两方面助推了社会对环保的漠视。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对当代人潜在的威胁并未得到识别与关注,他们更不会去考虑代际公平问题。
1.2.2 “浅绿色”环保观念的产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公害”事件频发,环境问题开始显露。1962年,卡尔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深刻探讨了自然的平衡和化学药物的危害,使环保观念逐步深入人心。1970年美国掀起大规模环保运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环保意识的集体爆发,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发端,直接促成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成立和环境立法,并推动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
此时,“增长无限”的观点也开始遭到质疑。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认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内发生”(米都斯等,1997)。虽然其中存在颇多理论缺陷,但它却是在“热增长”下的“冷思考”,用超越传统的思维,从系统角度重新审度社会发展,同时提醒人类关注资源和环境负荷。
这一时期,客观的现状和深刻的反思使人类开始从经济增长的盲目乐观中走向理性的回归。作为一种“浅绿色”的环境观念,环保理念日渐流行。
1.2.3 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
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和跨国性,依靠各国分散治理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走进了国际关系领域(孙凯,2001),联合国、经济组织及环保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等纷纷介入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革新以往“征服自然”的原始观念,提出人与自然合作的思想,并将眼光从代内延伸至代际,为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埋下伏笔。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WWF)共同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一词。同年3月,联合国大会正式使用该词。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将《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这一报告继承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的主体思想,正式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模式,即“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后,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被世界认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文件,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向高潮,会议文件对国家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约束,文件的通过成为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转折点。
可持续发展首次从人类发展方式的角度探讨环境问题,意在从根本上谋求不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对策,是由“浅绿色”向“深绿色”转变的关键抉择。然而从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至20世纪末,可持续发展实践一直未有较大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①可持续发展在认识上出现脱离经济的趋势,被视作环境伦理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造福后代的道德表达。②该理论尚处于进一步完善阶段,前景并不明朗,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谋求可持续发展会以减缓经济增长为代价(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Sterner and Damon,2011),从而出现消极抵触心理。③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具有内核文化的抽象性,尚不能对各国实践形成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1.2.4 可持续发展范式的涌现
由于片面追求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在推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的优先级被置于社会和经济之上,经济“零增长”(Meadows et al.,1972)和马尔萨斯主义一度受到推崇。实际上,这种可持续是单纯的“环境可持续”,但可持续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生态问题,也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而是三者共同的问题(Holling,2000)。
21世纪伊始,“经济”开始纳入可持续发展研究之中。从经济系统出发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是实践总结的经验教训,理论界也认识到经济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动力,脱离经济来谈可持续发展是不现实的。首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经济必须得到全面的增长(毕世杰,1999)。其次,可持续发展的抽象性决定其只能宏观指引,对实践难有实质的指导作用。加之经济利益始终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的结合是其过渡到实践的需要。*后,可持续发展只有具有可测度性才不至于沦为政治辞藻,而不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可测度性方面考虑,经济都是*佳的切入点。
经济正式进入可持续发展视野得益于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社会、环境,打破此前唯环境论的片面认识,使经济增长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持续发展也从片面重视生态保护的“环境可持续”过渡到以经济为切入点,经济、环境、社会三者并重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受益于此而得到快速发展。
由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模糊性,可持续范式便开始不断涌现,以便实施该理念(Nielsen et al.,2014)。在可持续框架下,以经济为切入点,不同组织、学者提出了如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等一系列可持续范式。
2001年Brown便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概念,标志着世界范围内以生态经济为主旋律的全球经济运动的开始。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不仅关注近期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也探究长期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以实现资源配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