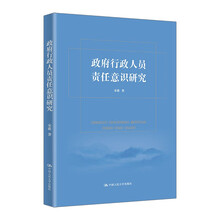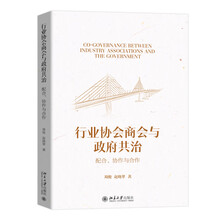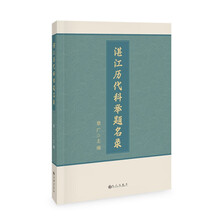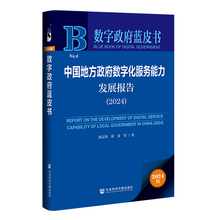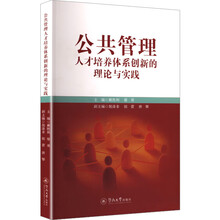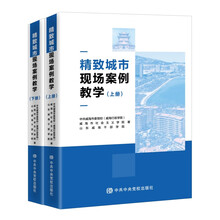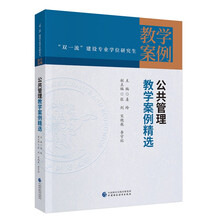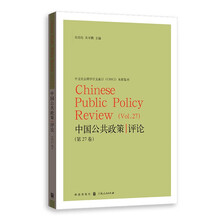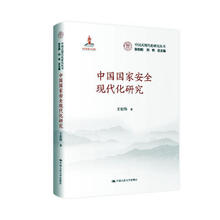中国的国家到底算是哪一类?这在近些年来再次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从现象上看,这是从2004年以后关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开始的一场知识运动 。虽然主要的参与者是学者,但学术讨论是大众社会思潮的反映。这种知识运动的发生,既是因为中国自己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因为中国相对于他者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晚清以来,我们多次都在这种变化的刺激下对“我是谁”变得敏感。所不同的是,我们第一次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自信心态。
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国家,中国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谁会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呢?最关心这个问题是必须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政府。“中国”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名词,可以解释成“居中的国土”。“华夏”可能是对于中国特性的最早的官方表述,《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各个朝代都会给本朝起一个名字作为“国号”。有趣的是,早期的朝代名字没有特别的寓意,甚至也不像百姓给子女起名字那样寓以美好的期待。它往往出自开国皇帝过去的封地、爵位甚至任职的地方,比如汉朝之所以叫做“汉”,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刘邦曾经被封为汉中地区的汉王。唐朝之所以叫做“唐”,是因为唐高祖李渊曾袭封“唐国公”,也就是说,古代的国号的意思是:皇帝本人或家族曾经是什么,名字即根基。这些名字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地方性,皇帝们老老实实地向天地报告自己的来历。但是到了后来,国号就越来越有寓意,包含了合法性论证。元代是一个突破,元代的“元”取之“大哉乾元”,她要做新的开端。明代的“明”寓意日月光明,朱元璋自许为是明教的明王降临人世。清代何以命名为“清”在今天是一个谜。到了中华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是王朝,也不再以当权者的来历为国命名,寓意就更加明确了。其寓意的方式可以理解成,以我们想要成为的社会状态作为我们的名字,名字即理想。
以往的朝代命名只在中国的历史中考虑问题,不必照顾周边的国家,到了民国和今天,就必须考虑在这个地球上“我是谁”,所以,国名中直接嵌入“中国”两字。同时,使用“中华”两字,也代表了对于历史的承续。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词就代表了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想要成为:一个属于人民的按照共和制来组织的继往开来的新中国。
对于中国是什么国家和社会,还有一些人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其他国家的商人、宗教传播者、学者或者政府。经过这一百八十年的接触和研究,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知识界和官方智库已经彻底祛魅。最明白的证据就是,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大都出自西方学术界,西方人成了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导师。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任务是,我们要在西方导师的中国研究的基础之上,努力创造出自己的理论阐释乃至范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理论虽然精巧,关于经验的整理虽然细密,对人类的关注也非常深远,却不会具体地对中国的未来负责。
中国学者用现代方法研究社会大致可以从1910年代算起,这一个时间点之前有一些重要的铺垫,如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和1905年废除科举,在废除科举之年的前后就开始有文科留学生的毕业归来。除了海外归来的学者,也有一些更加本土的思想者,比如1927年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1927年写出《中国文化史》的梁启超、1932年写出《乡村建设理论》的梁漱溟,等等。建国以后,社会科学的自由探索一度陷入低潮。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得到重建。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对于中国传统体制和文化的批判一时成为风潮。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2004年开始出现关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才算是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知识界开始用学术的方式表达社会中逐渐提升的自信心态。这种自信来自中国社会的持续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也受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感染。比如2006年完成的农村税费改革,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应对,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的举办,2012年以后的强力反腐败,以及中国政府在2020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全球大考验中的表现,都进一步地提升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的反思是比较早的,也比较成功。但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和过程的本土理解却是很难突破,这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领域,西方的思想家和学者已经经营了几百年。
尽管如此,中国学者还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展开了本土化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如王绍光主持的关于“理想政治秩序”的研讨 ,潘维主持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 ,甘阳等人关于“通三统”和古典文化的当代意义的讨论 ,赵汀阳关于“天下”的思考 ,还有关于政治儒学的设想,等等。 以上的研究多数是从哲学、政治学或者中国文化的视角中展开的。社会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的差异是它们很注重最基层的生活领域的经验,试图在宏观和微观的对接中把握中国社会的特质。人类学家王铭铭提出的文明是一个“超社会体系”的思考,试图对于中华文明的内在混杂性给出一个理论解释 。相比而言,黄宗智的研究是比较独特的,他是从历史学中的法律研究和农业经济研究推进到对于中国社会整体性质做出判断的,从而使得他的研究具有特别丰富的经验基础。 相关的研究还有不少,囿于笔者的阅读范围狭小,不能周遍地注意到。
在这本书中,笔者想要提出的是另外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特质的思路。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研究,尤其是要在这个流行“脱钩”的时代,研究中国社会中的上下联结问题。这个研究是从一类人们都熟悉的经验事实开始的,比如在中国的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对于扶贫对象的了解十分透彻。从家庭地点,家庭人数,住房与周遍环境,土地等资产,家庭的亲属关系网,邻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实际收入等等几乎所有这些都要了解,虽然不一定要记录在册,但要确保有人知道。因为所有这些对于精准扶贫的成效都有影响。当国家来如此把握群众的时候,群众就是具体的,或者说具象的。我们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依赖于和群众之间的人格化的日常联系。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国家是用这些日常联系替代了宏大的结构性互动,而替代的可行性来自独特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我把欧美的社会称为是“抽象的社会”,而采取这种依赖人格化的社会联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称为是“具象的社会”。
在如此巨大的中国社会中采取这种人格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必然要依靠一套复杂的结构,并依托独特的机制、丰富的资源和相应的文化观念才能实现。本书注重研究其中的结构,机制、资源和文化都作为理解这个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个结构也有一个现成的而且十分著名的词来表达,也就是“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一词的提出是中国人的制度自觉的结果。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能够给人带来想象空间的词,值得努力把这个政策提法发展成一个社会理论的术语。在描述中国的总体治理结构上先后出现过多种提法,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治理体系”的表述。在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完整提法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共建共治共享”是某些制度集成,但在本书中理解成是中国式治理体系的一个理想追求,要实现这个治理体系的这个理想状态需要依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治理体系”这个词的理论潜力不仅仅出自“治理”。“治理”这个词在英语中以governence出现时,代表了联合国开发机构对于受援国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提建议的角度,它替代了简单的选举式民主的方案,深入到制度运行的细节中。但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的“治理”之后,迅速激活了中国传统的治国智慧,人们发现,如果能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出发看问题,“治理”这个词实际上照亮了中国国家运行的长处。这确实是一次戏剧性的话语翻转。继而,有学者如曹锦清依据中国的治理实践提出了“治体”一词,作为替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政体”思维的新概念工具。他认为中国政治学“要将重点从‘政体’转向‘治理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学说史向来无政体一说, 重在治体, 而西方的学说重在政体, 轻于治体。西方以政体为中心的政治学说理论的研究源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说, 而中国政治传统重在治体, 它分为治道、制度与治术, 在这个论述上向来是儒法合流的。 本书也是将“治体”理解成“治理体系”的简称,就如同将“政体”理解成“政治体制”的简称。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链接上“治理”与“体系”这两个术语背后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脉络。
对于治理体系,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它整合社会尤其是联结上下的功能,研究以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整合的条件和普遍性意义。治理体系的结构不是本书的重点,这是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很多同行做过很好的探索,笔者在《体系: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和一些文章中也做过讨论,要说清楚它还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只能留待将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