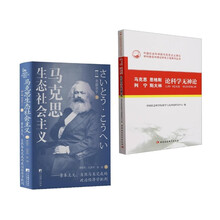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伟大的异乡人》导言
“从前,我读过很多被称作‘文学’的书。我扔掉了很多,看不下去,也许因为我没有掌握阅读的诀窍。如今(1975),一些像《在火山下》《西尔特沙岸》这样的书涌现出来。我很喜欢一位作家:让·德梅利耶。他的《乔布的梦》很震撼。还有托尼·杜威尔的书。说到底,在从前,对我这一代人而言,伟大的文学就是美国文学,是福克纳。似乎只有通过一种无法追本溯源的外国文学,我们才能进入当代文学,才能拉开与文学的距离。文学,曾是‘伟大的异乡人’(la grande étrangère)。”
1975年,在关于雅克·阿米拉《纳奥克拉提斯之旅》这本书(他先收到了邮寄过来的手稿)的访谈中,福柯极为罕见地描述了他的文学书单。我们能看到这份短书单的构成相当多元。他的阅读范围涉及像让·德梅利耶或雅克·阿米拉这 样的年轻作者,也有朱利安·格拉克这样的成名作家;此外,他也袒露了对托马斯·曼、马尔科姆·劳瑞、威廉·福克纳这些作家的欣赏,出于这种欣赏,他在1970年进行了一次从密西西比河谷到纳齐兹(Natchez)的寻访福克纳之旅。关于福柯的阅读经历,我们仍然所知甚少。根据他弟弟的说法,在他们位于普瓦图的童年时代的家中,竖立着两个风格迥异的书架:一个在外科医生父亲的书房里,摆放着学术的、医学方面的书,禁止触碰;另一个是母亲的文学书架,可随意阅览。福柯在母亲的书架上发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古典文学,而在教会学校里,他阅读了一些希腊文、拉丁文著作。也许是在乌尔姆街,在巴黎高师的神奇图书馆里,他才开始无所顾忌地阅读。巴黎高师图书馆是法国最早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之一,馆内藏有诗歌、哲学论著、批评文论、历史文献等各类书籍。在这座由莫里斯·布雷管理的图书馆中,他解构了一种话语秩序,文学出现在他眼前。达尼埃尔·德菲尔在《言与文》的年表中,给出了一些线索:福柯在1950年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 1951年阅读卡夫卡,1953年开始阅读巴塔耶和布朗肖,追随新小说运动(阅读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书),1957年夏发现了鲁塞尔(Raymond Roussel),阅读《如是》(Tel Quel)杂志的作者们,1968年1月重读贝克特。
我们不应忽视福柯自1956年起旅居国外的重要性。对乌普萨拉(Uppsala)法国之家(la Maison de France)和华沙法国文化中心(le Centre de civilisation française)藏书的日常阅读,也许极大加深了福柯与文学语言的紧密关系。在瑞典和波兰的孤独冬日里,福柯在进行大量阅读——夏尔(René Char)的诗集是他的枕边书——的同时也教授了很多文学课程。正是在这两地,在这两种对他而言陌生的外语中,正如我们所知,他进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他每周教授几个小时的法语,包括法国文学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课程中关于法国爱情主题文学的研究,研究范围从萨德(Marquis de Sade)直至热内(Jean Genet)。在瑞典,福柯曾主持一个戏剧俱乐部,带领学生们将一些当代戏剧搬上舞台。1959年在克拉科夫(Cracovie)和格但斯克(Gdansk),他做了几场关于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讲座。作为读者的福柯,还有一些经历更让人好奇,比如他在乌普萨拉期间曾遇见克劳德·西蒙、罗兰·巴特,以及来领诺贝尔奖的加缪。在晚年,他与一些年轻作家过从甚密,比如马蒂厄·兰东(Mathieu Lindon)和埃尔维·吉贝尔(Hervé Guibert)。见面的时候他从不“谈”(parler de)文学,似乎对于这些作家,他阅读其作品,却并不想跟作家本人发生对话,比如他从不去见莫里斯·布朗肖,“说是太欣赏他了,以至于不想认识他”。20世纪60年代初的福柯跟文学保持一种亲密关系,只要查看他为写作《古典时代疯狂史》而做的阅读笔记就能明白这一点。对监禁档案、比赛特(Bicêtre)精神病院登记簿以及国王密令的分析,首先是一种文学阅读的经验,关于这种经验,后来他 在与历史学家阿尔莱特·法尔日(Arlette Farge)合著的《家庭的无序》这本书开篇中进行了解释,该书发表了一些监禁档案资料。福柯着迷于这些档案的诗意之美、纯粹图式存在(existences graphiques)之美、他所谓的“17世纪以降文学坡线(ligne de pente)”之美。
然而,对于这种亲密关系,他一直采取否认态度。比如,他在1963年写了整整一本关于雷蒙·鲁塞尔的书,在讲述如何遇到鲁塞尔的作品时,他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在科尔蒂图书馆(librairie Corti),“我的目光被一套书吸引住了,黄色封面,有些老旧,上世纪末的出版社传统上会使用这种颜色。(……)我发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作者:雷蒙·鲁塞尔。那本书叫作《视》(La Vue)。刚读几页,我就觉得这本书文笔极其优美”。
“伟大的异乡人”实际上是隐姓埋名的过客。因为福柯不仅是严苛的读者和文笔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问世之时,文风都会受到欣赏和认可。作为哲学家,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构成本书的资料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是一种复杂的、批判性的、战略性的关系。只要仔细阅读他的文字——不仅局限于他的著作,也包括《言与文》以及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课——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如果我们阅读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关于文学的各类序言、访谈、讲座(根据布朗肖、巴塔耶等人的术语来组织,或相反,试图用一种作者理论或一种关于语言空间的总体描述来重新审视文学 批评的传统元素),如果我们记得这些文本不仅是对他那些考古名著的强调补充,也在这些名著内部产生局部共鸣——比如当他提及俄瑞斯忒斯或《拉摩的侄儿》(《古典时代疯狂史》)、萨德(《临床医学的诞生》)或塞万提斯(《词与物》),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种文学关注的独特性。如果说福柯在某种程度上与整整一代人态度相一致,如果说他也延续了法国思想中一种坚持的姿态,即力图让小说或诗歌成为哲学思考的试金石(巴什拉、萨特、梅洛·庞蒂轮流接受过这一考验),福柯的文学关注看上去像是自身话语的一种真正重复(redoublement)。重复,或更确切说是永恒替身(doublure),也即以极端方式,尝试同时言说某一既定时期的世界秩序及其表象秩序(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福柯在其研究中对一种“思 想体系”的考古学描述)以及与之矛盾的,对世界之过度、越界、域外(dehors)维度的表象。他早期的重要著作,尽管面向不同的特殊对象(疯癫、临床医学、人文科学的诞生),都分析了同一主题,即我们关于世界的话语,其组织方式如何受到既定历史时期一系列划分(partages)的影响。相反,他在同时期关于文学的著述似乎展现了一系列奇怪的形象——执拗的作家、冰冷的话语、写作迷宫,若非是为了表现对上述主题的明显拒斥,至少是为了表现显著例外。唯独一种情况下,“著作系列”(ligne des livres)与福柯的文学文本系列有所交叉:《雷蒙·鲁塞尔》。唯独在这本书中,历史的和知识型的研究似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恰是关于话语秩序为何失序的隐秘观点:也许是因为一种行为——写作的行为,但也是因为另外某种东西,这种东西直接包含着一种要将文学作为战略来占有的方式。在这一时期,福柯处处倾向于同时支持两种立场,一种立场在于否认文学的特殊性,另一种立场则强调文学的战略中心地位。在第一种情形下(考古学式研究),相对于其他话语产物(行政文书、契约、档案资料、百科 全书、学者著作、私人信笺、报纸……),文学并不具有任何特殊性;第二种情形(“文学”文本)则意在说明,在文学内部,一种姿势(posture)和各种写作手段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些写作手段因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进行的,会导致某种类似于无—序(dés-ordre)经验或断裂行为的东西,比如一种变化模式或一种变形操作。总之,一方面是词与物之间强烈的关联,另一方面是一种奇怪的论断,即能被言说之物有时却无法被思考。从此,这一奇怪的分离让众多实验成为可能,在实验场域中,话语(discours)能够超越自身规则或超越它所指之物的单义性:“鲁塞尔之谜,在于他语言(langage)的每个成分 都取自一个充满无数构型可能的系列。这一秘密比布勒东暗示的秘密更明显,却更为艰涩——它并不在于对意义的玩弄,也不在于各种揭露的把戏,而在于形态的一种审慎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 concerté de la morphologie),或者说,在于确信多种建构能够形成同样的文本,而同一文本允许存在互不兼容、各行其道的阅读系统,这是形式之严格而不可控的多功能性。”
关于这一主题有两点说明。一方面,对福柯而言,相对于他自己的分析,文学所代表的这种“域外”与一个自愿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享有这一令人眩晕的形式多功能性,让我们的世界秩序滑向它自身混沌深渊的,并非文学本身,而是负载文学的行为:将文学作为战略,也即对文学的某种利用、诸种手段的实施以及叙事布局内部的一切爆破工作,这一爆破工作经由反意义霸权的战场建设而达成。另一方面,这一“域外”超越了布朗肖此前赋予该词的定义,也超越了福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借用该词时的定义—对“我思”与“我言”二者分离关系的观察以及语言向自身外部不确定的缓慢渗出,超越在于,文学这一“域外”还直接确定了话语逃避表象王朝的另一种存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些物质手段得以施行,来建构这些结构顽固的言语—根据不同情形有:无法听清的、荒谬可耻的、无法归类的、无法被翻译的、无法论证的、碎片化的、偶然性的、不稳定的、令人眩晕的言语。
20世纪60年代末,跟文学的这一奇特关系似乎消失了。原因也许有很多,我们在此试举三种。
第一个原因:话语相对于其他实践形式而言,不再具有特殊地位。话语秩序是一种(历史给定的)世界秩序:它是我们组织跟事物、跟我们自身、跟他人关系的模式之一,但它并不代表着一种独断的模式。有时,话语秩序先出现,创建了其他划分(例如一种制度的诞生、某种对身体的干涉、一种社会隔离),有时话语秩序似乎是其他划分的结果。同样,对文学的某种利用,其“无序”只是打破世界秩序的诸多尝试之一,存在着其他战略,比如不通过写作进行的言说、“引导自身行为”的种种方式,都对世界秩序进行了斩断、质疑或爆破。就此意义而言,福柯逐渐放弃将文学领域视为自身研究的“替身”,这一放弃也许归因于他有意要将自己的疑问延伸至一个更大的主题——这次是以权力和抵抗的形式提出的。被用作战争机器的文学写作,很容易 在其中找到自身位置,不过它已经不再代表着问题的唯一范式。
第二个原因:我们很难对一种决定做出说明。我们刚才提到对文学的利用和写作手段:这里必须要有主观意愿,涉及的必定是一种意图。然而根据旧观点——也许仍然是现象学回忆下的重要观点——只有在文学和疯癫 交叉之时,才能形成足以“解开”语言的那种言语,在这一观点的笼罩下,很难去辨识意图问题。一位像路易·沃福森或让—皮埃尔·布里赛这样的作者,其意愿是什么呢?那种意愿什么时候才是彰显的?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从“监狱信息小组”(GIP)时期所代表的另一种言语经验开始——似乎让福柯越来越感兴趣的东 西,或者说向集体维度的跨越,这究竟是什么?如何将无—序(无论是有关语言规范的解构、对某一制度的拷问还是 对自己身份客体化的拒斥)与一些被划分的实践联系在一起?那些实践不仅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主体性,也构成了多种跨主体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原先是追问某些“文学个例”对既定秩序的逃避,现在转变为更广泛地研究政治抵抗方式:就此意义而言,战场的低沉轰鸣绝非一种文学比喻。
最后,第三个原因在于对“域外”意象的放弃,这一点得到福柯的直接承认(域外是一种神话),以及对历史内部— 权力关系内部、同时被发出与被承受的词语内部、被粉碎的意象内部、无论如何人们不断再生产的意象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异这一主题的重新投入。于是问题增多了:在某一种知识的和历史的形态内部,在某一既定时刻由某种话语和实践结构展开的“真实网络”内部,总而言之,在一种既定历史的世界语法内部,我们如何能做到挖掘和颠倒发音、改变字行、移动标点、挖空意义、重塑平衡?这一问题当然是理论性的,但也直接是政治性的:在让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也就是说,以我们思考的方式来思考、以我们说话的方式来说话、以我们行动的方式来行动)的这一历史内部,我们能否摆脱这些限定,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安排出一种言语和生活方式的别样(然而总是在内部)空间?然而,正是从文学研究中产生的这一问题,将不断萦绕在福柯心头:可能的超越与决定我们之所是的历史限定,不应处于对抗状态,而应在共可能性的模式上进行思考—从此,我们跟巴塔耶珍视的僭越或布朗肖的“域外”相去甚远了。
本书中收录的福柯言论是从这一角度来选择的:它们出现在这套丛书里绝非偶然,均为口头演说,时间跨度少于十年——1963年至1971年,但每一篇都跟写作和语言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前两篇是1963年1月法国电台播放的两期节目,它们被完整收录进来。福柯在节目中选用了很多文学片段: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狄德罗、萨德、阿尔托(Antonin Artaud)、雷里斯(Michel Leiris)……
第二份资料由1964年12月在布鲁塞尔连续两场关于“文学和语言”的讲座构成。第三份资料是1970年在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演讲的未发表手稿,由两部分组成,主题为关于萨德侯爵的研究,他多次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至少三次),手稿均得到保留。将这三份资料收录在一起,并非对一种强行言说的无主题语言之讽刺,也并非对我们乐 于呈现给读者的一种被迫言说的白色写作(écriture blanche)之讽刺;相反,这部分体现了回归书面的一种多形态焦虑,这种对话语的外部性、物质性和狡黠性之焦虑。福柯没有明确表态是其始作俑者,但在一段时期内他曾成为这种焦虑的扩音器。
菲利普·阿迪耶、让-弗朗索瓦·贝尔、马修·博特-博纳维尔以及朱 迪特·雷维尔
(Philippe Artières, Jean-François Bert, Mathieu Potte-Bonneville & Judith Revel)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