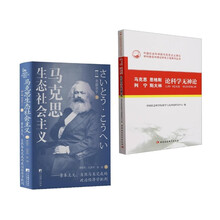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童年
虽然我不是饱学之士,也不是个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有时甚至觉得连自己是否可算知识分子也是个问题,但我毕竟在这知识分子的队伍里,靠着一支笔、几张纸头和笨拙的舌头领着微薄的工资,并用它维持我一家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半生,我退休前的所谓的职业。
也许是命中注定了我要走这条路,当我刚满周岁的时候,父亲就希望我做个知书识礼的人。在他,自然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现在,我感到别扭。依才智,我总觉得自己并不是做老师的料,常为自己可能误人子弟而后怕,并且还常常为需应付简单的生活而苦恼。但是,父母亲已经感到了很大的满足,虽然他们没有从他们这个当老师的儿子这里得到任何一点好处。他们仍然过着艰难的生活,平日里要拖着老朽的身躯为生活而劳碌,但是他们感到幸福,感到快慰。在他们看来,要让儿子成为文化人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村里人非常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子“有出息”。他们在人们面前走过的时候,带着一种荣耀感。所以,尽管在生活上没有得到我任何的照顾,他们仍旧很高兴,很满足。
听父亲说,我满周岁那天,家里就在我周围放上银钱、毛笔和杆秤之类的东西,让我抓周,对我自己的命运进行占卜。这些东西以相等的距离放在我的周围,看我自己先去抓什么,据说先抓什么就说明将来要从事那个行当。如果先抓的是银钱和杆秤之类的东西,说明长大了是个生意人;如果抓的是酒瓶和脂粉之类,难免是个酒色之徒。也许真有些道理,我竟抓了笔,这使我的父母亲喜出望外。他们杀了一头猪,请了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为我庆祝第一个生日,庆祝我将来会成为拿笔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在父母亲的心目中,我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了。父亲料定我会给这个从未有人进过学校的家庭带来光荣。
所以,在我刚能拿稳毛笔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写字。无论怎样忙,他每天都用红土研成红墨,在草纸上为我写好几篇字,让我描红。父亲的字写得并不好,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我总是认真地去完成父亲给的这一作业。
我们家住的是一幢三间的茅草屋,已经很旧了,橡子上和楼板下吊满了尘灰条。屋子没有窗户,大白天进去也是黑黢额的。一些房柱子已经腐朽,在上面拍拍,可以听见“啪啪”的响声,还时常听得到蛀虫在柱子里发出“嗡嗡”的叫声。
晚上睡在这种屋子里,周围一片漆黑,无一丝光亮。睡下之后,父亲总是边抽他的老旱烟边给我背《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目前杂字》以及其他一些他能背出来的文章,并讲述他学习的艰难情形。记得有一次,背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时,他突然停下来给我解释说,“日参省乎己”就是说三天剪一次手指甲,并说起先他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便跑去问一位读书人,那个人是这样告诉他的。现在回忆起来,很有趣。我不知道那位读书人是真的这样理解这句话,还是故意耍弄我的父亲,反正我父亲深信不疑,并把这种谬误传给了我,我自然也是深信不疑的。当时,我只是想,三天剪一次手指甲太勤快了,一般人做不到。还有,这剪手指甲的事也能这样写到书里,让人们反反复复地读吗?自然,我也只是想想罢了,没有问父亲,也没有问过其他的什么人。直到我自己会读古文了,也读到“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了,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终究没有向父亲说明过。父亲不背书时就给我讲故事,或是点起明子火,侧身坐在床头,歪着身子在枕头旁那张从地主家分来的书桌上练习珠算。我躺在床上静听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声,慢慢地进入梦乡,往往几次醒来都还听到父亲一边一个劲地背着口诀,“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一边手不停地在珠子上拨动着。我父亲的算盘打得很好,加减乘除样样精通。他经常给我讲各式各样的珠算运算方法,例如什么叫“调尾乘”,什么叫“破头乘”,怎样使用顶珠和底珠,等等。有时候下雨,做不成活计,父亲就用一个方形的红凳支起算盘,坐在火塘边练习珠算,并时时讲给我听。每到这时,我母亲便端出针线箩子静静地坐在旁边,边做针线活边听我们父子说话,并不时用针在乌黑的头发上抿一下。有时父亲讲得深了,她便插一句,说我还小,听不懂这些。
现在回想起来,这时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是何等重要,时隔几十年,许多事还记忆犹新,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当时背过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现在大都还记得。这些东西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在我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时,我就背《百家姓》,这种办法曾在几次考试中助我摆脱了尴尬的局面。
P2-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