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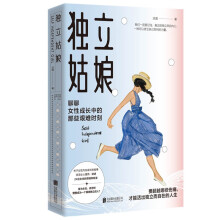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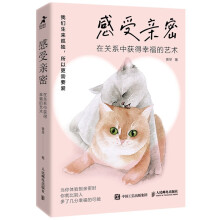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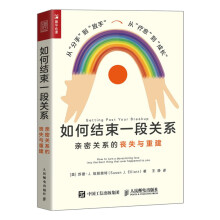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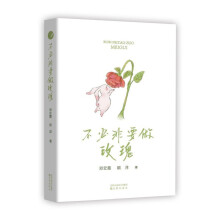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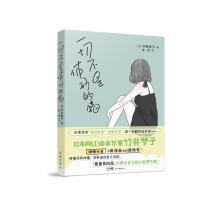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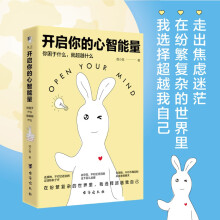

本书探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生:不依赖他人的、不囿于母职的、不惧怕衰老的。莫娜•肖莱认为“女巫”是唯一通过自身来持有某种能力的女性原型,不因其他人而被定义,所以,作为这种力量的承继者,现代女性也可以独立生活,自然老去,掌控自己,这种探讨和思考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本书曾荣获2019年《心理学杂志》散文奖(Prix de l'essai Psychologies-Fnac 2019)。
猎巫运动曾为我们打造了某种令人恐惧的女巫形象:她们施行邪术,她们顽固不化,她们衰老丑陋……然而,这首气势磅礴的意识形态之诗遍布着厌女情绪的韵脚,其余风依旧浸染着当今世界对女性的评判。莫娜.肖莱为我们除去了掩人耳目的矫饰,呈现出真正的“女巫”形象:她们独立生活,她们自然老去,她们掌控着自己的身体与性。
这里探讨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生:
不依赖他人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缺失,而是可以建立关系,但这些关系必须尊重我们的完整性、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全面绽放,而不是自我束缚;
不囿于母职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只是让日子变得有希望,都得先让生孩子变成随心所欲、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一件事;
不惧怕衰老的——女人并不是非得保持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她们完全有权利用另一种面貌、另一种美丽来丰富自己。
“女巫”是唯一通过自身来持有某种能力的女性原型,她不因其他人而被定义,所以,“女巫”的继承者们,请承继这种力量,为自己而绽放吧!
将这一辈子活成你们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
导论 女巫继承者
说起女巫,人们一定会想到华特.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里的那一位: 黑色风帽下是一头泛白的亚麻色头发,鹰钩鼻上长着一颗肉疣;咧嘴笑时,滑稽地露出一颗仅存的下门牙;邪气的眼睛上方缀着一对密匝匝的眉毛,愈发衬得表情不怀好意。但对我童年影响最深的并不是她,而是回暖日的蓬蓬婆婆(Floppy le Redoux)。
蓬蓬婆婆出现在《被偷小孩的城堡》里。这是瑞典童话女作家玛利亚.格瑞普(1923—2007)写的一本童书。故事发生在某块幻想出来的北欧地区。蓬蓬婆婆生活在一座小山顶的房子里。房子顶上罩着一棵老苹果树,老远就能瞧见这棵老树在天边的剪影。这地方宁静又美丽,但邻村的人都尽量避免踏足此地,只因为这里之前立过一座绞刑架。到了晚上,人们能看到在那栋房子的窗户上有一道微光。那是这位老妇人在纺布。她一边纺着布,一边和她的乌鸦索隆(Solon)聊天。索隆是只独眼乌鸦。它往智慧井(Le puits-de-la-Sagesse)里探了一下身子,就丢了一只眼睛。最打动我的并不是这位女巫的魔法,而是她散发出来的气韵:静谧、玄秘,又洞悉一切。
她的行头让我着迷:“她出门时,总是裹着一件宽宽大大的深蓝色斗篷。斗篷的大领子迎着风,围着她的头,发出蓬蓬的响声。”蓬蓬婆婆这个绰号由此得来。“她也会戴一款奇特的帽子。高高的帽顶是紫色的,上面装饰着几只蝴蝶。从帽顶上垂下几朵花,散布在软软的帽沿上。”人们在路上碰见她,都震慑于她那双蓝眼睛里的光芒。“那双眼睛不时变换着光彩,着实有种魔力。”或许就是受了回暖日的蓬蓬婆婆的形象影响,后来当我接触时尚时,我蛮欣赏山本耀司那些带着压迫感的作品。他的衣服是宽宽大大的,帽子也大到没边儿,像是布料堆起来的避难所。这种审美与主流背道而驰。在主流审美中,女孩们应裸露尽可能多的肌肤,解锁尽可能多的穿衣方式。在我的记忆中,蓬蓬婆婆像是一个护身符、一道仁慈的阴影,给我留下了女人可以何等大气的最初印象。
我也爱她的隐居生活,还有她与社群的关系: 既疏离又暗自关联。婆婆的房子所在的那座小山,仿佛保护着那个村子,“就像把它拢入羽翼之下”,作者玛利亚.格瑞普如是说。女巫是这么织着超凡的毯子的:“她坐在纺织机前,一边沉思一边劳作。她的思绪围绕着村民们与他们的生活。直到有天早上,她发现,她预见了他们要发生的事情。她凑近织匹,从她指下自然流淌出来的花纹中读出了他们的未来。”当她难得又短暂地出现在村里的街道上时,路人就看到了希望。之所以叫她“回暖日”——这也是个绰号,因为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就是因为她从不出现在冬天。当她再出现时,就预示着春天快要到来了,即使她出现那天的气温是零下30度。
不管是《亨塞尔与格莱特》(Hansel et Gretel)里的糖果屋女巫还是慕夫塔街(rue Mouffetard)的女巫,抑或是俄国童话里住在鸡脚小木屋里的芭芭雅嘎(Babayaga)女巫,这些让人不省心的女巫们带给我的感受永远是兴奋大过排斥。她们激发着你的想象力,带来一阵醉人的战栗,带着你去冒险,奔向另一个世界。小学下课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在学那个居住于院子灌木丛后头的女巫,借此来重拾在冷漠的教育体制下日渐麻木的自我。危险感助长了雄心壮志。你会突然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人畜无害的标致与清风拂面的和善并不是唯一可想象到的女性命运。少了这份晕眩感,童年就少了点儿滋味。因为蓬蓬婆婆的存在,女巫之于我绝对是一个积极的形象。她掷地有声,惩治恶人;她让你感受到报复那些曾经看低你的人所带来的畅快淋漓。有点儿像鬼马小精灵(Fantômette),但婆婆是用她的精神力量,而非穿着体操紧身衣的小精灵所使用的体操技巧:因为我讨厌运动,所以女巫那一套甚合我意。透过她,我曾经想过,作为女性,或许还有另一股力量加持。但那时候也有一个模糊的声音提示我:或许正好相反。从那以后,无论在哪个角落看到“女巫”这个词,我总能被瞬间吸引住,仿佛它宣示了“我”体内一股潜在的力量。这两个字眼咕嘟咕嘟地冒着能量的泡泡。它让人想到某种接地气的学识,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力量,某种被正统学问蔑视或排斥但却在现实中被反复证明并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也喜欢将其视为某种艺术,让人穷其一生精益求精、倾注所有热忱的艺术。女巫代表着跨越所有支配、所有限制的女性;她趋近至柔,她指明道路。
“今人之牺牲品,非古人之牺牲品”
我曾经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在我所接触到的文化产品中,关于女巫超能力的描写包含着过分渲染的奇技淫巧以及有关人物形象怪异的误解。要知道,“女巫”这个词在成为想象催化剂或荣誉称号之前,曾是最糟的耻辱符号,是莫须有的罪名,曾为数以万计的女性带来酷刑与死亡。猎巫运动这段发生于欧洲16—17世纪的历史在集体意识中占据了奇特的一角。关于巫术的判词都集中在某些怪诞的诬告上: 比如夜间飞行去参加巫魔夜会,再比如与魔鬼合谋或与魔鬼通奸。这些罪状仿佛把她们拉入了非现实的领域,将她们剥离了真实的历史。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个骑着扫帚的女人的形象,来自马丁.勒.弗朗(Martin Le Franc)的《女性冠军》(Le Champion des dames)(1441—1442)的手稿空白处,其姿态轻佻且滑稽。她像是从蒂姆.波顿的电影里跳出来的,或是从《神仙俏女巫》(Ma sorcière bien-aimée)的片头里,又或是从万圣节某个装饰物里蹦出来的剪影。但当时,她在1440年前后的出现揭开了几世纪痛苦的序幕。当史学家吉·贝奇特(Guy Bechtel)说到巫魔夜会这一形式的诞生时,曾写道:“这首磅礴的意识形态之诗杀伐无数。”至于性折磨,其真相想必都消解于女巫在人心中激起的淫邪之相与骚动不安里了。
2016年,布鲁日的圣让博物馆(Musée Saint-Jean de Bruges)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勃鲁盖尔的女巫”的展览。勃鲁盖尔这位佛兰德斯大师是第一位围绕女巫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的画家。展览中的一块壁板上罗列着几十位本市女性的名字,她们被认定为女巫,在公共广场上被火刑烧死了。“布鲁日的许多居民至今还沿用着这些女性的姓氏。但在参观这场展览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先人曾经被指控行巫。”馆长如是说。说这话时,他面带微笑,仿佛祖上有个倒霉鬼因为旁人几句妄语就一命呜呼是件无伤大雅、可以随意和朋友聊起的轶事。我不禁想问: 还有哪一项大众之罪,即便是久远到如今已不复存在,却能让人这般云淡风轻、嘴角噙笑地谈起?
猎巫运动曾让数个家族满门被屠,制造了恐怖统治,无情地压制了某些至今仍被视为无法忍受的异端的行为与活动。同时,这一运动也参与塑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如果猎杀女巫不曾发生,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将大不相同。这段历史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关于人们做出的抉择、享有特权的方式以及那些被处决的女人。然而,我们拒绝直面这段历史。即使我们接受了当时的某些现实,但我们总能找到法子将这场运动远远搁置起来。因此,人们常常将其错放到中世纪时期,把发生的背景描述成一个久远晦暗的时期,与我们毫无关系。但其实几场重大的猎巫行动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大致始于1440年,1560年后渐渐扩大声势。甚至到了18世纪末仍发生了几次处决女巫事件,包括对安娜.果尔迪(Anna Göldi)的处决,她于1782年在瑞士的格拉鲁斯被斩首。吉.贝奇特曾这样评价这位女巫:“她是今人之牺牲品,非古人之牺牲品。”
与错置时间线类似的是,人们还经常将这些迫害归咎为宗教狂热,认为其执行者是丧心病狂的宗教裁判官。然而,旨在镇压异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却极少追捕女巫。绝大部分的处刑都是由非宗教法庭裁决的。对于巫术,这些世俗法官看起来“比罗马教廷还要残暴与癫狂”。不过,在一个除了正统的宗教信仰之外不允许“边缘”存在的世界里,裁决法庭的世俗与否,意义也不大。即使有几个声音蹿出来反对此类迫害——比如1563年有位叫让.维埃(Jean Wier)的医生,发出了“满池皆是无辜血”的呐喊——也再没有人质疑魔鬼是否存在。至于新教徒们,即使他们看上去理性得多,但在追捕女巫这件事上却与天主教徒有着同样的狂热。宗教改革所倡导的回归对《圣经》的字面解读并没有唤醒宽容,结果是适得其反。在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有35名“女巫”被处决,就因为《出埃及记》里有这么一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让她存活。”当时宗教大环境的排除异己以及宗教战争的嗜血屠杀——1572年,在巴黎的圣巴托洛缪,有三千名新教徒被杀——喂大了两大阵营的残忍胃口。
说句实在话,正因为猎杀女巫这段历史讲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才更有理由不去直视它。如果踏入这一雷池,就意味着我们要直面人性中最绝望的一面。首先,它揭示了社群的顽固不化: 隔一段时间就要为自己的不幸揪出一只替罪羊,自我封闭在非理性的漩涡中,不接受任何理智的辩驳,直到民怨四起,怒不可遏,最终诉诸肢体冲突,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是社群机构出手进行正当防卫。另外,它也揭露了人的某种能耐。这种能耐用弗朗索瓦丝.德.;欧本纳的话说,是“用疯子的理论来大开杀戒”。将定性为女巫的女性妖魔化与反犹主义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女巫的集会被说成“巫魔夜会”或是“犹太式聚会”(synagogue);她们和犹太人一样被扣上疑似密谋毁灭基督教的帽子;另外,她们的形象和犹太人一样,都被赋予了同款鹰钩鼻。1618年,在科尔马(Colmar)镇旁的一次女巫处决中,百无聊赖的书记员在笔录旁的空白处画上了被告女巫的形象: 她的头饰被画成了传统犹太式的,“戴着大耳坠,满头的六芒星饰物”。
通常情况下,替罪羊的指定,远不是一群粗鄙贱民可以操控的,而是来自高层,来自有教养、有文化的阶层。女巫传说的诞生几乎与印刷同时,后者诞生于1454年。印刷术也在猎杀女巫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贝奇特在书中提到了“当时用到了所有信息渠道”的“传媒联动”:“给识字的人发书,给其他人讲道,给所有人发大量的图画。”两位宗教裁判官[阿尔萨斯的亨利.因斯托里斯(l’ Alsacien Henri Instoris,德语名为Heinrich Krämer)与巴塞尔的雅各布.施普伦格(le Bâlois Jakob Sprenger)]于1487年推出的大作《女巫之锤》(Le Marteau des Sorcières)在发行量上可媲美阿道夫.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这本书再版了15次,共发行了3万多册,流通于全欧洲各大阶层:“在那个烈火熊熊的时代,在每次审判中,法官都要用到这本册子。他们会问出《女巫之锤》里的问题,也将听到《女巫之锤》里给出的答案。”以上史实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印刷术最初运用的理想化预设……《女巫之锤》锤实了“危难在即,须用非常手段”的念头,让大众陷入集体幻觉中。它的成功催生了一种名为魔鬼学的行当,其驱魔除邪的题材倒成了图书业的一个金矿。那群写出魔鬼学“著作”的人——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在其文字间表现得像一群愤怒的疯子,但其实他们都是些博学且声望甚高的人。对此,贝奇特嗟叹道:“对比他们在其魔鬼学行文中表现出来的盲从与粗暴,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目 录
致谢
导论 女巫继承者
“今人之牺牲品,非古人之牺牲品”
有女过界者,斩其首
一段被否认或虚幻化的猎巫史
从《绿野仙踪》到《精神之舞》
暮光里的女巫
猎巫史是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的
艺术与魔法:激发女性的力量
第一章 自己过活:女性独立的灾祸
福利大婶、女骗子与“自由电子”
女冒险家,禁忌典范
反抗者须知
火刑架的阴影
谁是魔鬼?
不想被“消融”的女人:自己定义自己
“服务”的本能反应
“母性镣铐”
第二章 不育之欲: 无子,也是一个选项
奔向其他出路的冲动
关于(不想)生育欲的微妙变化
缺乏思考的区域
对女性生育自然观的挑战
发现生命的“林间空地”
不可接受的生育言论
最后的秘密
第三章 顶峰之醉: 打破“老巫婆”形象
春归人老
“人心自有它的道理”
对固有形象喊停
当女性开始回答时
边界的女卫士
“卑劣”的专属形象
被妖魔化的女性欲望
“创造另一项法律”
第四章 将这个世界翻转过来——向自然宣战,向女性宣战
“‘在哪方面’卓越?”
自然之死
德勒夫、坡坡科夫与别人
女子之言不足信
潜在团结的诞生
把病人当人看
当不理智不在人们以为的那一边时
另一个世界的雏形
“疯女仆”的造反
想象一下,同时进行两场解放
“您的世界不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