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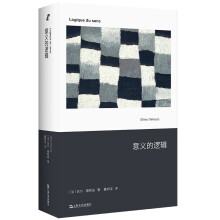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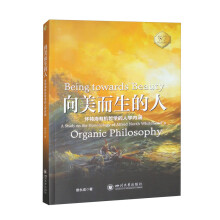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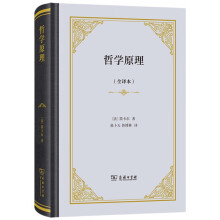

“快与慢”文丛之一
灵魂与自由意志问题,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论域上承中世纪神学与经院哲学遗产,下启现代哲学之滥觞,为认识论转型和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灵魂与自由意志/“快与慢”文丛》:
进而,说理智灵魂总共只有一个单独的能力,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依赖于而另一种不依赖于身体,这也很荒谬。不然,它看起来就好像具有两种存在方式了。一种理知,即便是理智和灵魂,并且在其理解之时并不需要身体,可它还是会需要身体来致动,但在某个地方致动和理解是非常不同的功能。而且,理智被置放于灵魂之中,前者依赖于身体,而后者则是无条件绝对的。这似乎不能和理性相协调,既然这一种单独的功能,相对于同样的东西,似乎肯定是一种单独发挥功能的方式。
况且,要总数为一者能够在同时对同一客体具有几乎无限的功能似乎也是没有必要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就是随当前观点推论而出的。那个理智能够通过一个永恒的理智而认识上帝,并且通过一个和上帝相当的新理智,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理智,也便都能够认识上帝。现在,这似乎像是一个纯然的虚构,从很多理由都可以看出来。然而,如果一种理知能够无需身体来认识,但不能在一个没有身体的地方致动,那前后就无甚矛盾可言了;既然认识和致动是非常不同种的功能,且一个是内在固有的,而另一个是过渡的,那么在考虑到理智灵魂的时候,完全的对立面就出现了。因为二者都是理智,又都是内在固有的功能。
其次,关于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根据亚里士多德理智灵魂是真的非质料的,就像评注家所声称的那样,既然这本身并不是立马可知,而是相反地极度值得怀疑的,那就应该有一些证明来说明这一点。不过,已经足够推论出其不可分性了,根据亚里士多德,它要么是一个器官性的能力,或者,如果不是器官性的,那么至少其活动的发生不能没有一些身体性的客体的帮助。因为他在《论灵魂》第1卷条目12中说过,无论理智是想象力,还是不能无需想象力,其分离都是不会发生的。既然,不管怎样,可分性是不可分性的对立面,而一个分割的肯定命题也与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一个联结的肯定命题相矛盾;那么如果不可分性足以表明,其不是作为在一个主体中的一个器官,便是在一个客体之上而依赖于器官,那么对于可分性来说,就同时要求既不在一个主体之上而依赖于一个器官,并且也不能在客体之上如此,至少在其活动的某个器官上如此。既然,不管怎样,这就是成问题的,阿威罗伊怎么能确信灵魂是不朽的呢,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都说了,一个人在认知之前是需要有一个心象的,而且每个人都在其自身之中经验到了这一点?
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说,对《论灵魂》第3卷的论辩无条件地证明了灵魂是非质料的,因为它接收了所有质料的形式。由此,可以严格地推论而出,它的活动可以全然独立,既然活动发生在存在之后。
不过,这似乎并不靠谱,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论辩预设了理智是由身体所驱动的,既然他说认识不过就像是感觉,而潜在理智是一种消极能力;进而,他说其推动者是一种幻象。但是,需要一种幻象的东西与物质并不可分,理由已经被给出了。故而,这一论辩证明的反倒是它是质料的,而不是非质料的。
但是,仍有可能可以这么说,因为理智不需要一个器官作为主体,所以它是无条件非质料的(这一论辩亚里士多德直接地在上述观点之后给出)。可这似乎并不能有所促益,因为要么这种情况是独自足以满足条件,要么就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它不由身体所驱动。如果二者兼具,前面的论点便成立;如果一者独立,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判断便被摧毁了,既然他坚持要二者兼备。
然而,或许依然可以说,实际上只需要其中一者。因为需要作为一个主体的身体并不必然隐含着他是一个非质料性的能力或者反过来说的意味。因为无论如何,除了是非质料的,它也许有一些活动是全然独立的(因为,实际上,如果它是非质料的,那它就会有一些独立的活动,反之亦然)——既然无论如何,有可能除了有一个活动独立于任何客体之外,它还有一个活动是不独立的;更别说还有可能有人会想到,既然它有一些不独立的活动,那么它所有的活动就都会是不独立的了,于是,亚里士多德补充道:“如果认识不是无需想象力的话”,那么它就在每个活动中都需要想象力,从而理智也就无疑是不可分的。
……
彭波那齐《论灵魂不朽》导言
论灵魂不朽
瓦拉《关于自由意志的对话》导言
关于自由意志的对话
费奇诺《关于心灵的五个问题》导言
关于心灵的五个问题
译后记:意大利文艺复兴哲学家的三种面相
人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