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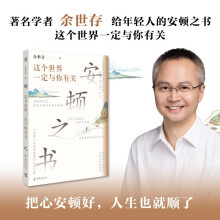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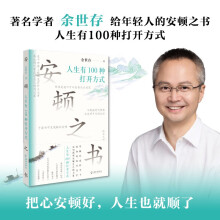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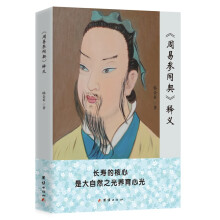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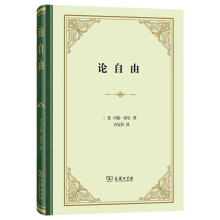

绩效是新自由主义的剥削方式,也即自恋主体的自我剥削,在一种停不下来的行动和竞逐中,产生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心理病症。
“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一对概念,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时代背景、她的思想脉络中鼓舞行动的生命,反映出当时社会和知识人群的精神面貌,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日益深陷多动和过劳的熟悉信息时代,一种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的生活节奏对“劳作动物”来说,也许更加有益。
韩炳哲骨子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派,这一点在对诺瓦利斯自然主义观念的追溯中暴露无遗。人类不应该将自身看作神与万物之间的代理人。在放下欲望和盲动之后,人类才能消除孤立、分隔和疏离,迎来一个和解与和平的时代;才能成为一个“生命体共和国”的公民,在那里,人与植物、动物、石头、云、星无异。
绝对的存在之缺失
当前的危机在于,一切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和方向的东西都在断裂。生命不再由那些具有持守力量或可持守的东西负载。里尔克《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中的诗句“无处停留”,最恰切地表达了当前的危机。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短暂,易逝,易朽。
汉娜·阿伦特曾说,“永久”(Unvergänglichkeit)已经“从人类周围的世界中消失,正如它从世界周围的自然中消失”。与此同时,她在“人心灵的黑暗中,为夜找到一个暂时的容身之处”,它仍然有能力“回忆,并且说:永久”。最易逝的存在,即有朽的人,已经成为“永久最后的庇护所”。阿伦特引用了里尔克的一句诗:“山休憩了,被繁星笼罩;/ 但,时间也闪烁其中。/ 我狂野的心中沉睡着 / 无处为家的永久。”阿伦特引用的这句诗,事实上是在感叹存在一刻不停地消退。诗的第一节写道:“消磨时间!一个美妙的词汇。/ 持守时间,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谁不害怕:/ 哪里有停留,哪里终将有存在?”
今天,人的心已无法为永久提供一处栖身之地。如果心是记忆和回忆的器官,那么在数字时代,我们完全没有了心。我们储存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却不再追求记忆。我们背离了任何形式的永远,发誓断绝那些耗费时间的行动,比如忠诚、责任、许诺、信任和义务,而让暂时、短期与无常主导生命。
时间本身也逐渐遭到瓦解,仅剩一连串点状的现时。它变成了加法。没有任何叙事使它成为一个图像(Gebilde),让它停下脚步。时间架构遭到侵蚀。仪式和节日正是这样的时间架构,它们在飞逝的时间里加入支架和关节,让它变得稳固。今天,人们正在逐步拆除这些支架和关节,因为它们阻碍了信息和资本的加速循环。
世界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导致了时间的碎片化,并彻底让生活变得转瞬即逝。存在具有时间维度,它漫长而缓慢地延伸。今天的短暂性则拆解了存在。存在只会凝结在驻留中。人不可能在信息身边驻留,因为信息代表了存在绝对的萎缩阶段。卢曼曾对信息做过如下评论:“信息的宇宙论不是存在的宇宙论,而是偶然性的宇宙论。”存在崩解为信息。我们的注意力只会在信息上稍作停留。之后,信息就会像录音电话上的留言一样归零。信息的实效范围极为狭窄。它们激起人的惊奇,又让人在信息流中应接不暇。
人是一种叙事动物(animal narrans)。然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由那种能带给我们意义与方向的叙事决定。这样的叙事能够起到联结的作用,并且具有约束力。我们接触的信息非常丰富,但由于缺乏叙事,我们迷失了方向。如果像尼采所言,人的幸福取决于有一个“不容讨论的真理”,那么我们的确没有幸福。真理是一种叙事,信息则是一种加法,因而无法凝结成叙事。信息加强了数字的偶然性风暴,也加剧了存在的缺失。没有什么能保证自身具有约束力和持久性。增加的偶然性破坏了生活的稳定性。
今天的世界极度缺乏象征物。象征物可以建立稳定的时间轴。象征式的感知是重新认出事物的方式,可以看到事物长久的存在。重复使得存在具有了深度。象征式的感知不再受制于偶然性。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序列式的感知,后者只能发现一个接一个的信息点,因而数据和信息没有象征力。
象征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知,在前反思、情感与审美层面上影响着我们的行动与思考。象征制造了共有之物,使得一个社群中有可能产生“我们”,产生凝聚力。只有通过象征和审美,才能形成共感(Zusammenfühlen)、同情(Sym-Pathos)与合情(Ko-Passion)。相反,在没有象征物的地方,共同体碎裂成冷漠的个体,因为不再有任何起联结作用或有约束力的东西。由于失去象征物而导致的同感丧失,加剧了存在的缺失。共同体是一个由象征物联系起来的整体。象征—叙事的空洞会带来社会的分裂与侵蚀。
柏拉图的《会饮篇》(Gastmahl)让我们了解到象征的真正含义。阿里斯托芬在这篇对话中讲到,人最初是球形的生命。由于人变得越来越强大、高傲,诸神就把他们劈成两半。自此以后,两半中的每一半都在追求与另一半的结合。被劈成两半的人在希腊语中被称为“符木”(symbolon,象征)。作为符木的人渴望得到一个幸福的、有治愈力的整体。这种渴望就是爱。有待合二为一的整体治愈了伤口,消除了存在的缺失,这样的缺失源于最初的断裂:“象征……理解象征物意味着,这个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像存在的碎片一样呈现出来,与它匹配的另一半要与它结合,以达到治愈和形成整体的目的;或者意味着,这个能形成整体的、一直被追寻的碎片,是我们生命片段的另一个片段。”象征物是对存在之丰盈、对治愈的承诺。离开象征式的秩序,我们只能以碎片和片段的形式存在。
今天,我们把最大的力气花在了延长生命上。然而事实上,生命已崩解成生存。我们为了生存而生活。无论对健康的歇斯底里,还是对优化的狂热追求,都反映出存在的普遍缺失。我们试图通过延长赤裸的生命来弥补存在的缺失,但却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对有深度的生命的全部感觉。我们把生命与更多的生产、更多的绩效和更多的消费混为一谈,而这些不过是生存的形式。
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造成人与人的隔离,这也导致了存在的缺失。孤立和孤独带来存在的缺失,因为存在是“共在”。新自由主义的绩效社会中不存在“我们”。新自由主义制度通过将人孤立起来,并使人经受残酷的竞争来提高生产力。它把生命变成求生存的斗争,变成狂暴的竞争营造的地狱。成功、成就和竞争都是生存的形式。
数字化也拆解了作为共在的存在。被网络化并不等同于被联结。恰恰是这种毫无边界的连通(Konnektivität)削弱了联结。密切的关系要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而他者是不可支配的。然而,在数字网络的推动下,我们把“他者”,即“你”,变成了一个可用的“它”,由此带来一种源始的孤独感。一个能满足我们需求的、可消费的对象,并不允许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网络化和连通性不断增强,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
当我们用爱欲的(libidinös)能量占据一个客体时,就会产生一种密切的联系。但心理能量的回流致使它们不是流向他者,而是流回自我。这种心理上的回流,也就是未被占据的爱欲的拥堵,造成我们的恐惧。恐惧源于缺少与对象的联系。“我”被抛向自我,围绕自我旋转,没有世界。缺席的爱欲加剧了存在的缺失,而爱欲足以战胜恐惧和抑郁。
存在的缺失触发了生产的过剩。今天的过度活动和过度交流,都可以被解读为人们对普遍的存在之缺失所做的反应。物质的增长成为抵消存在之缺失的方式,于是我们通过生产来对抗缺失感。生产或许位于存在的零点。资本就是生存的形式。资本主义由这样一种幻觉滋养:更多的资本创造更多的生命,带来更多的生命能力。然而,这样的生命是赤裸的生命,是生存。
匮乏感是行动的驱动力。果决地行动的人不会去观照(schauen),而像浮士德那样感叹“请等一等,你如此美!”的人,并不行动。在直观中,人得以抵达作为美的存在之丰盈。人们已全然忘记,至高的幸福归功于直观。无论在古代还是中世纪,人都是在沉思的直观中寻觅幸福。古希腊诗人米南德(Menander)写道:
我称他为最幸福者,帕尔梅农,
那没有经历过痛苦,
就能观照世上荣光的人……
为所有人照耀的太阳,星辰,
大海,浮云,火的光芒:
若你寿数达百年,你会不断看到这一切;
若你的生命仅有寥寥数年,
则你无法看到比这更高的存在。
当被问及为什么来到这世上时,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回答:“为了静观(Schauen, eis theorian)。”出生时,我们从没有客体的黑暗中被释放出来,进入光明的世界。新生的人之子睁开眼睛不是为了行动,而是为了静观。不是对新事物的激情,而是对现存事物的惊奇,确立了生而为人的意义。出生意味着看到世界的光。对荷马来说,生命与“静观太阳的光”一致。
行动的生活固然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在托马斯·阿奎纳看来,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沉思生活的幸福:“行动的生活是为沉思的生活所做的安排。”沉思的生活是“整个人类生命的目的”,沉思的静观则是“对我们全部追求的回报”。作为行动的成果,一件作品只有在它呈现给直观时,才算真正得以完成。
托马斯·阿奎那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的评注中给政治下了一个独特的定义。他提出一种无所事事的政治,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方式与阿伦特的政治观截然相反。如果政治没有向非政治敞开自我,那么它终将是一场空。托马斯·阿奎那所理解的政治,其最终目的在于不作为,在于直观:“政治生活在整体上所指向的似乎就是直观的幸福,也即和平。和平在政治生活所设立的目标上得以建立和维系,它能够让人全身心投入对真理的沉思中。”
面对完满的存在,人只能去直观,去赞美。因此,在神圣的安息日来临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融进了赞美诗的语言。安息日向世人许诺了“无目的的”上帝之国。但人在永恒的天国里做些什么呢?“我们将在永恒中得享清闲”,奥古斯丁欢呼道,“看,看”,“爱,爱”,并且“赞美”。“这就是,”奥古斯丁继续道,“有一天在那无目的之目的中会成为的人。”看与爱在奥古斯丁这里融为一体。“爱所在之处,眼睛才会打开。”看与赞美是无所事事的形式,它们不追求任何目的,也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有存在的缺失才会驱动生产的机器。
赞美是语言的最终目的。它赋予语言以节日的光辉,扬弃了所有存在的缺失,歌唱并唤起存在的丰盈。里尔克曾在一首诗中将赞美升华为诗人的任务:“哦,说吧,诗人,你做什么?——我赞美。”在诗人的赞美中,语言达到了节日般的、沉思的安宁。赞美是语言的安息日。在赞美中,有朽的人心中闪耀的“有限存在”发声了:“赞美,就是它!一个命定去赞美的人,/ 像矿藏从石头中走出,/ 沉默。他的心是易朽的榨汁器,/ 而葡萄酒对凡人是无尽的。/ 当神性的榜样抓住了他,/ 他在尘埃中发出的声音就从未间断。一切都变成了葡萄园,一切都变成了葡萄,/在他感性的南方成熟。”
里尔克将赞美与广告区分开来:“不再是广告,不是广告,那被抛弃的声音。”广告中有一种固有的缺陷,一种属于纯粹生命的缺陷,也是以操心为本质特征的“烦忧动物”(kümmernden Tier)固有的缺陷。赞美则摆脱了所有的追求与操心,它的节日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存在缺失之处,赞美也无立足之地,只剩嘈杂的广告声。今天的交际从整体上看是纯粹的广告,是一种生存形式,它的燃点就是存在的零点。
节日的时间属于更专注的静观。“节日感”则是程度更深的存在感。节日创造了意义与方向,从而照亮了世界:“节日打开了日常的此在之意义,开启了人周围的物之本质,以及人的本质中蕴含的力量。节日作为属人的世界里的真实……意味着在有节奏地循环往复的时间段里,人能够安闲沉思,直接与更高的真实邂逅。人的整个存在都依托于这个更高的真实。”节日的时间永不消逝,我们走进它,就像走进一个装饰隆重的房间。它是珍贵的时间(Hoch-Zeit,意为“婚礼”)。节日带来恒久(Zeitlosigkeit),所有存在的缺失在恒久中都得到了清偿。
工作将人与人隔离开来,使人变得孤立。工作和绩效的绝对化拆解了作为“共在”的存在。节日则创造出一个共同体,聚集着人,联结着人。节日感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一种“我们”的感觉。伽达默尔将节日理解为共同体的基础:“节日是共性(Gemeinsamkeit),也是共性本身最完美的表现形式。”
当直观还是人与世界相处的基本方式时,人与完美无缺的神性存在之间仍有联系。希腊语的theoría(静观)最初指的就是去远方出席诸神节日的使团。theoría意为对神性的静观,theorós是参加节日的使团,theoroi是众神的观众。节日般专注的静观,让观众变成参加诸神节日的使团:“当埃斯库罗斯不用theatés而用theorós指代观众时,他指的是一场更大的、无上庄重的静观。”哲学家关心神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众神的观众。亚历山大时代的学者哈波克拉底(Harpokration)这样描述众神的观众:“被称为theoroi的不仅有众神的观众,还有被派往众神那里的人,更有那些持守神的秘密或为神的事物操心的人。”亚里士多德将静观的生活(bíos theoretikós)提升到神性活动的高度,并在沉思的生活中找到完满的至福时,他思考的视域中无疑出现了theoría一词。它描述了人对神迷醉的静观:“亚里士多德最终没有把哲学家的直观等同于任意的静观,而是把它类比于对奥林匹亚众神的直观,或者对狄奥尼索斯节日的静观,因为‘众神的观众’确实是被派遣到众神那里的。亚里士多德在此发现了与偶像崇拜无关的神性。”
人之所以能进行静观的生活,是因为他“身上带有神性”。亚里士多德明确强调,众神不行动:“我们认为,众神拥有最大的幸运与福乐。但什么样的行动可以归于神的名下呢?或许是公义?但如果让神订立合同或退还保证金,诸如此类的事情岂不可笑?或许是勇气?比如他们不得不直面恐惧,接受危险的考验,仅仅因为它是一种壮举?又或许是慷慨?但众神应该向谁赠予呢?如果他们必须给人财物或类似的东西,那简直有些荒谬。然而节制对于众神又有何意义呢?‘没有不良的欲望’这类描述对众神来说无异于一种粗俗的赞美。因此,我们可以任取所需。所有属于德性实践的东西,在众神面前必然显得渺小而毫无尊严。然而,人们却认为众神在生活,也就是在行动。没有人想到,他们像恩底弥翁(Endymion)那样沉入睡眠。但假使我们从活着的人那里拿走行动,尤其拿走睡眠,那么除了静观,人还剩下些什么?”神的活动,也就是“有至高福乐”的活动,即静观的活动。与政治的生活(bíos politikós)相反,静观的生活不行动,也就是说,它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静观的生活是无所事事,是沉思的安宁,是悠闲(scholé)。生命在无所事事的悠闲中指向自身,不再与自身疏离。亚里士多德因而将静观的生活与自足联系在一起:“即使是被称为‘自足’的东西,也往往是在静观中寻得。”只有沉思的生活才能承诺神圣的自足与完满的至福。
在行动完全让位于静观,让位于无所事事的安息日那一刻,历史得以完成。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看到一个人在艺术作品前全神贯注的样子后,果断做出这样的哲学假设:“如果说人所有的追求以及整个历史有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是在静观中获得圆满。”
无所事事的面向 1
《庄子》旁注 29
从行动到存在 33
绝对的存在之缺失 53
行动的激情 67
来临中的社会 97
注 释 113
附录 韩炳哲著作年谱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