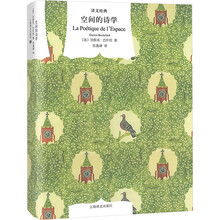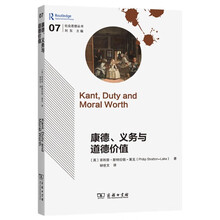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雅克·拉康,过去与现在:对话集》:
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是的,这种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尤其是在巴黎。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家是庸俗唯物主义的信徒。他们对记忆、情绪、自我、自恋障碍,以及正常和异常行为感兴趣,他们认为所有超出了最起码的临床框架的东西都是推测性的,因此是危险的:这与行为心理学已相距不远。然而,拉康在理论和实践上使摆脱这种看法成为可能,因为它强调的是语言,关注的是言说,以及处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核心位置的切割的必要性。他没有局限,他尊重病人的职业,并且不纠结于治愈或者正常化的理想。
在这个时期,正统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家呼吁拉康的学生选择他们的阵营,并将精神分析变成一种解释性的宗教。相反,拉康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思想:比如当一位神父来找他做分析——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他会建议他继续当神父,如果当神父是他的真实欲望的话。这是因为拉康理解精神性的本质——以及哲学的本质——所以耶稣会士尤其会对他感兴趣,尽管他是无神论者,并且完全地遵循科学辞说的严谨性。这种以干瘪的、实证主义的方式重读弗洛伊德的生物学模式,极大地阻碍了那些前来寻求治疗的宗教人士。
阿兰·巴迪欧:实证主义往往是一种倒置的宗教,以至于它非但没有为它所声称的科学服务,反而被意识形态的目标所奴役,而这些目标与科学自身的未来是格格不入的。鉴于此,宗教人士比科学本身更有理由害怕实证主义。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认为上帝是热爱科学的,而并不爱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
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的确是!他们也被在弗洛伊德那里宗教与神经症的相似性所拒斥。事实上,法国的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家大部分是反教权者、实证主义者,他们对知识或精神性活动几乎不持开放态度,也很少倾向于哲学的辞说。由此许多耶稣会士皈依——尽管我不太喜欢这个有着如此内涵的词——到拉康的思想当中。然而,拉康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倾向于一种教条式的概念,即主张超短程的治疗,挫败感甚至欺诈就来自于此。极力批判诉诸情感、热衷于结和数素的形式体系的原教旨主义拉康派的危险是对病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一个理论越是革新性的——拉康的理论极为如此!——,它就越是可能在某个时刻跌入教条。拉康主义也不例外。
哲学杂志:阿兰·巴迪欧,拉康意义上的治疗呈现出特有的哲学意味吗?我们感到它潜在地实现了您所谈及的对主体的革新。
阿兰·巴迪欧:治疗是种行动,它既设定、。同时也穿越了形式。当下讨论的这种形式是无意识的客观结构。然而在提到这些结构的时候,是治疗对它们进行切断并将之分割成部分。对于拉康来讲,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治愈”——他在这点上相当节制;精神分析需要走向某个实在的地点,在那里主体能够重新站起来并获得新生。精神分析让被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转变了方向,并且重新开启了主体的能力。我一直认为拉康本人对此的定义十分绝妙:“治疗的目的是将无能为力提升为不可能。”“不可能”指的是拉康意义上的“实在”,即永远不会被符号化的东西。因此,做分析被看作是去打破某个最初让分析者感到无能为力的局面(我背离了自己的欲望,被生存的无情和停滞给困住了),而引向某个实在的位置,在此本来陷入想象的主体能够恢复一部分自己符号化的力量。
在哲学的层面上,这个构建完全是了不起的。从形式(无意识的结构)的角度来看,行动(治疗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保持着可被理解的同时,同样也穿越了这些结构。在精神分析中会发生某件事(主体面对着一个实在的位置),但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件事,就不得不将它放在其形式的背景当中。尤其到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拉康对我来讲就是一位哲学的英雄,因为他避开了两个障碍:一方面,他脱离了平庸的决定论,因为他提出在治疗中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切断;另一方面,他非常坚决地与精神性的或宗教的教义保持距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切断并非是某种奇迹——它与无意识的理性形式直接相关。
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不管是对科学主义还是对蒙昧主义,拉康都不予理睬。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