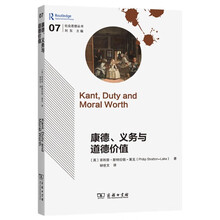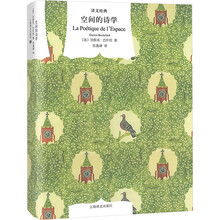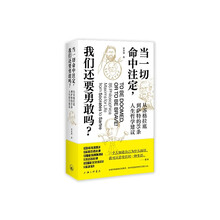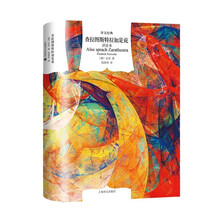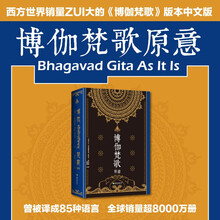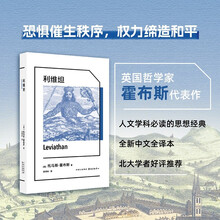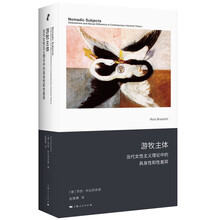《指称、语境与语义学》:
激进语境主义面临的一个主要指责是,如果不存在最小命题、真值条件语义学和系统的语义理论,如果所有的词项都是语境敏感的,那么每个句子的真值条件内容都不是系统可预测的,那么说话者说出的语句就具有意义不确定性,这样无法保证说话者和听者能获得相同的语义内容,交流也就成为不可能的。最小主义者认为,如果不存在最小的语义内容,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如何能够通过基本的字面内容把交流意图传递出去?言语行为内容的确可以是丰富的、随语境变化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载体作为交流的公共部分。开普兰和勒珀和一些温和语境主义者如索莫斯等都主张句子的语义内容就是该句子在各种被说出的场合中所交流的内容的公共部分,此即最小命题。
对于激进语境主义,由于不存在语义内容的共享,就必须用别的方法来解释成功交流如何可能。激进语境主义者通常对此持有一种松散的标准,只要求说话者表达的命题与听者所理解的命题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关系,以便保证交流能够继续进行。例如,对于从物思想的交流,雷卡纳提主张成功的交流需要在说话者和听者之间保持语言学呈现模式的相似性,AnneB则认为需要在对话双方保持关于指称对象的心理学呈现模式的相似性。不管成功交流的标准是什么,说话者和听者在成功的交流中必定分享了某些内容。要获得这种共享的内容,说话者和听者还需要有一些共同的背景知识。雷卡纳提强调有三种因素来确保交流内容的共享:(1)说话者和听者具有相同的心理结构;(2)对话双方对陈说内容的相互理解中的互动;(3)对模糊性和误解的容忍。这些因素排除了共享最小命题作为成功交流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某些语境敏感的词项的语义值的确定似乎要依赖于说话者的意图,而说话者的意图无疑是难以被句法系统编码的。这是命题主义最困难的地方。博格试图论证,在表达式的指称确定的过程中不能离开说话者意图但是对句子的语义内容的把握则无须借助说话者意图。对于包含指示词等语境敏感词项的句子,听者只要能识别出表达式的特征或语言学意义就足以完成语言学的理解。对陈说(言语行为)内容的把握,不是语义学的任务。这里,又回到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系和划界问题。
斯坦利曾经给出语义/语用区分的三种方式:(1)语义学研究相对于语境保持不变的意义。在这种区分下,“I”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值属于语用因素。在这种区分里语义学处理的是表达式的类型。(2)将语言学解释分为语义阶段和语用阶段。语义阶段处理表达式的语义值,这需要结合句子的逻辑形式和语境。语用阶段通过会话准则如相关性、质的准则和量的准则,不涉及根据语句结构来确定语义值,本质上不是语言内的因素而是外语言的因素起作用。在这种区分下,语义学处理的是相对于语境的表达式。(3)语义学处理句子的真值条件或命题,即真值条件语义学。语用学研究以真值条件命题为输入的情况下,言语行为中蕴涵的命题。其中第一种区分是格莱斯以前的区分,为早期的不少理想语言学派的提倡者所主张,如蒙太古等。后两种区分是温和语境主义者也接受的主张,如果斯坦利关于逻辑形式的理论是合理的,那么第二种和第三种区分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意图对于句子内容的贡献就不会是语义贡献。
事实上,说话者意图与交流内容的关系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的层面而与理解的心理学密切相关。激进语境主义者认为最小主义者强调的最小命题并未在交流过程中出现,因此是多余的。在交流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直觉性真值条件,这一真值条件不依赖于前述所谓“自下而上的”过程通过句法和词汇的习规意义产生,而是借助于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背景信息的共享、听者领会了说话者的交流意图而产生的。根据雷卡纳提,在交流中真正进入意识层面的只有通过语用过程产生的直观性真值条件内容,由于最小命题并未进入意识层面,对于交流内容的真值条件的解释也是多余的,因此可以完全抛弃最小命题。真值条件的意识可达性应当成为确定“所断言的内容”的标准,雷卡纳提强调,应该用心理过程的方法来理解真值条件内容,也即将真值条件内容(语义内容)当作“潜在于理解中的复杂处理过程的有意识输出”,而不应该从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语义内容,即把真值条件内容当作经过饱和过程之后得到的最小命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