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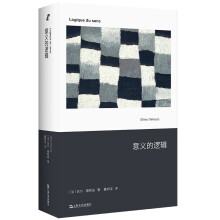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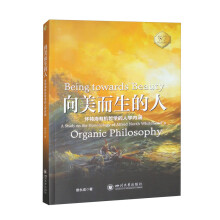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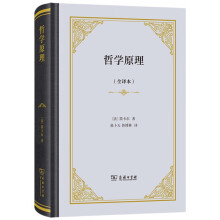

本书卖点
1.研读胡塞尔哲学代表作《笛卡尔的沉思》不可或缺的经典导读。《笛卡尔的沉思》是20世纪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生前发表的三部现象学的导论性著作之一,它是胡塞尔哲学晚期的代表作,是影响深远的西方哲学经典。本书精选自劳特利奇出版公司的经典书系——劳特利奇哲学导读丛书,是对《笛卡尔的沉思》一书的专业导读。
2.导读对原著阐释精当,重点突出,且文风朴实,化解了原著晦涩难懂的尴尬。本书对胡塞尔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如悬搁、绝然性、同感,等等都做了专门的说明与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所关涉的先验现象学的重要问题做了恰当、细致的说明,同时还结合胡塞尔的其他相关著作进行佐证研究,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非常广阔的现象学图景。此外,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常常结合日常生活的事例加以说明,令人感到既亲切又熟悉,使胡塞尔的通常颇为费解晦涩的理论透彻了许多。
3.忠实于文本,脉络清晰,方便与原著对照阅读。不同于市面上其他大多关于哲学家思想概览的著作,本书结构编排总体上因循了原著的架构体系,返回哲学文本,按照各篇的内容依次进行阐述,方便读者与原著对照阅读,逐章节读懂经典。
4.人大哲学教授倾情翻译,精益求精,做到了翻译精确的同时语言流畅。本书由人大哲学教授赵玉兰老师翻译,译者参考多种胡塞尔著作的中译本,确定书中多数关键性现象学术语,同时对少数关键性术语的译法做了调整,并在“译序”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5.装帧精美,版式舒朗,便于阅读。
编辑推荐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学习胡塞尔的哲学,就离不开对他的哲学原著的研读。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胡塞尔的原著有多艰涩难读。尤其是《笛卡尔式的沉思》原文论述过于言简意赅,专题讨论所涉内容铺陈过大,表述方式欠妥,专门术语缺乏说明,等等。这些问题让你迫切需要一本既能够帮助你降低阅读难度,又不失精准的导读作品。本书正是基于这一目标而写的。
本书对《笛卡尔式沉思》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是研究此书经典的导读读本;译文精准且通俗流畅,既适合哲学研究者阅读,又适合普通哲学爱好者阅读。
本书适合跟《笛卡尔式的沉思》原著对照阅读。本书并不是对原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而是分章节,针对其中的关键概念、术语进行阐述,所以,建议读者先自己阅读原著一整章文本,然后再阅读本书对它的分析。或者,试着仔细阅读本书对一章的分析,然后再看对应的原著。
胡塞尔与笛卡尔
前面关于胡塞尔观点的阐述——它以古希腊人的真正哲学思想的起源为特征,这一起源已经在我们的传统中积淀下来并且变得“虚幻不真”,因此我们必须尝试原初地彻底思考它,从而使它复兴——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想起马丁·海德格尔。诚然,有人提出,尽管胡塞尔不承认,但是他的这种视角其实是源于海德格尔的,并且胡塞尔(只)把它引入到了晚期著作《危机》之中,而《危机》在时间上是晚于海德格尔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的。然而,当读者们想起上面的阐述主要来自《存在与时间》出版之前胡塞尔所发表的那些演说时,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得出我所持有的结论,即实际的(以及大量未被承认的)影响恰恰方向相反。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胡塞尔对哲学史的解读事实上与海德格尔迥然不同,它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根本上把哲学的“原创建”回溯到了柏拉图,而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已经代表了对真正原初的思想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背离偏移。其次,胡塞尔指出,笛卡尔是哲学史上的第二块重要的里程碑,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在笛卡尔那里,这种偏离已然恶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这种分歧背后的原因是极其深刻的。说完了这些,我们不妨把视线转向笛卡尔。
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导论性的前两节中,胡塞尔把我已经详细说明的、包含在哲学“理念”中的所有内容都归结于笛卡尔。我先前的阐述之所以聚焦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是基于以下这两点理由的。首先,正如我所表明的,胡塞尔本人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因此,当他把对“在绝对洞见基础之上的终极奠基”(44)的关注归结于笛卡尔时,他并不是指这样一种哲学关注源于笛卡尔。其次,有一个问题被胡塞尔研究者在通向现象学的“笛卡尔式的道路”(Cartesian way)的名目下讨论着。《笛卡尔式的沉思》,以及《观念Ⅰ》和某些其他著作,被认为是仅仅提供了朝向先验现象学的一条可能路线,对此,并不存在非“笛卡尔式的”选择。事实上,甚至是《笛卡尔式的沉思》本身——它在总体上遵循着“笛卡尔式的道路”——也谈到了“一种达到先验现象学的道路”(48,我做的强调),而另外两条道路,虽说有些简略,也被具体地指出了。我们稍后将考察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对绝对洞见、无条件的辩护和普遍绝对真理的关注——简言之,对“严格科学”的关注——并不能构成通向现象学的“笛卡尔式的道路”。因为一方面,它并不是独特的笛卡尔式的:胡塞尔在某一处把它称为“柏拉图式的与笛卡尔式的理念”(EPⅡ,5)。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胡塞尔本人确实明确谈到了通向现象学的“笛卡尔式的道路”,并把这种道路与其他道路进行了一番比较。但是对于胡塞尔来说,并不存在柏拉图式—笛卡尔式的视角的替代品:那种视角才正是真正哲学的本质!著名的胡塞尔研究者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他实际上在胡塞尔晚年期间担任着他的助手——却不以为然(Landgrebe 1981,Ch. 3),他引用了胡塞尔晚期的一个文本,其中写道:“哲学作为科学,作为严肃、严格、甚至绝然严格的科学——这个梦该结束了。”(Crisis,508[389])然而,虽然胡塞尔的确写过这些话,但它们并不是他自身思想的表达。这种观点是由一个想象的反对者表达出来的——“这正是这些人普遍的主流意见”(同上,[390])——这句引文所出自的那段话的全部矛头所向就是要抛弃这种思想,它与胡塞尔的全部计划是前后一贯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观点“淹没了欧洲人”(同上)。
但是,如果“哲学作为严格科学”并没有使笛卡尔与众不同地成为哲学上一个彻底全新的阶段的开创者,那么哲学做了什么呢?在胡塞尔看来,与柏拉图不同,笛卡尔“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把数学当作了哲学知识的范式(参见Crisis,第8节,第16节)。但是正如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所说的,那是一个“致命的偏见”(48—49),而不是为他增益荣光的东西。在某些段落里,胡塞尔似乎主张,在笛卡尔那里既富新意又具价值的东西就是对绝然“洞见”的强调——所谓绝然的(apodictic),就是指可以被如此绝对地证明其正当性,以至于对其思想内容的否定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事实上,虽然胡塞尔在涉及笛卡尔以及包括他自己哲学在内的后笛卡尔哲学时,确实极为频繁地谈到了绝然性,但是在他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讨论中,这个概念也并不是踪迹全无的。譬如,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以“完成于绝然自明性之中的有助于澄清的自身反思”为特征的(EPⅠ,11)。而且,至少侧重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胡塞尔无疑认为,虽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可能已经探求了作为其哲学“理念”一部分的“绝然性”,但是只有通过笛卡尔,我们才拥有了实际上允诺为我们传来福祉的哲学的彻底化。因为胡塞尔认为,原初的希腊哲学创建涉及某种“素朴性”。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思想的无可争议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克服这种素朴性的那个必要步骤,该步骤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根本特征。笛卡尔的这个独特成就就是塑造了“一种转向主体自身的哲学”(44),一种转向意识主体、转向“自我”、转向“我”的哲学。笛卡尔试图“有史以来第一次揭开……必然回归自我的那种真正的意义,进而克服早期哲学探讨的潜藏的、却已隐约感到的素朴性”(48)。更确切地说,认识到主体、人自身的意识自我是无可争议的、绝然确定的存在,简言之,是著名的笛卡尔的“我思”(Cogito),这正是笛卡尔的历史功绩之所在。事实上,正如胡塞尔在别的地方提到的,对他而言,笛卡尔并不是认识到意识主体的本己存在的绝对无疑性的第一人。正如早在笛卡尔时代的批评家所指出的,我们在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那里就已然能够发现这种思想。因此,更为确切地讲,笛卡尔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以向不容置疑的自我“回归”作为对抗怀疑论的唯一可行之道。只有怀疑论才肩负着“迫使哲学迈上朝向先验哲学道路的伟大历史使命”(EPⅠ,62)。在胡塞尔看来,由于怀疑论提供了把希腊人导向哲学原创建的刺棒,因此,这种朝向自我的回归此时便首次作为哲学的必然的第一步而与笛卡尔联袂登场了。这是笛卡尔的《沉思录》的“永恒意义”。它们“表明或试图表明哲学开端所具有的必然式样”(同上,63)。或者,正如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所说的,“它们为所有开端哲学家的必然沉思树立了典范”(44)。
事实上,胡塞尔认为,在笛卡尔的思想中,唯有“我思”在根本上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每当他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譬如EP I,63;Crisis 76[75])提到笛卡尔的《沉思录》时,他几乎总会提到前两篇沉思:这两篇沉思借助于有条理的怀疑,独立地考察了向自我及其“思想”的不容置疑性的回溯。而对于笛卡尔的后四篇沉思,胡塞尔甚至不会多看一眼。因此,读者就不必奇怪,与笛卡尔的六篇沉思相对照,胡塞尔的沉思却仅有五篇。《笛卡尔式的沉思》绝不是关于笛卡尔著作的评论或指南。相反,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法兰西最伟大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通过其《沉思录》赋予先验现象学以新的动力”(4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早在17世纪就赋予先验现象学以这样的推动力。在那时并没有先验现象学,它是胡塞尔本人的发现。胡塞尔的意思是,在20世纪前十年,阅读、反思笛卡尔的著作为胡塞尔本人向这种现象学前进提供了新的动力。《笛卡尔式的沉思》是对这种影响的认可,是对笛卡尔的著作与先验现象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认可。但它并不是一部关于笛卡尔的著作;它本身是关于先验现象学的著作;只不过笛卡尔曾经发起的一次转向与之相关。
虽然胡塞尔谈到,笛卡尔著作中的这种向自我回归是彻底全新的,甚至是开创新纪元的、世界历史性的事件,但是,正如读者现在应该能够评判的那样,胡塞尔仅仅把它视为哲学生活的彻底化,这种生活最早作为人类的一种可能性而随着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出现。之所以说它是这样一种哲学生活的彻底化,首先是因为,一旦哲学家独自开始他或她自身的意识生活,就必须独立地从那个视角进行哲学探讨,那么,自身负责的原初要求就成为哲学方法不可避免的特征。那时,任何“发现”就必然地“作为他的智慧,作为他自身获得的知识而产生”(44)。其次,自我的自为的生存此时就提供了一个关于绝然性、错误的不可思议性的具体基准,哲学知识中的任何随后的收获都必须与之相符。然而,这些因素并不构成笛卡尔步入主体性的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胡塞尔认为,这一步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因为虽然笛卡尔并没有在这一步中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他已经偶然发现了先验主体性,并且使得先验哲学成为可能。进一步理解对于哲学来说什么是先验的,它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笛卡尔为何并且如何无意间发现了这条通向哲学的最终彻底化的道路的,这正是第一章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