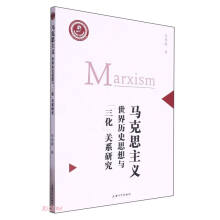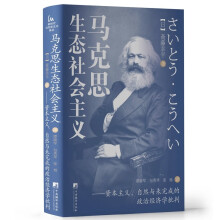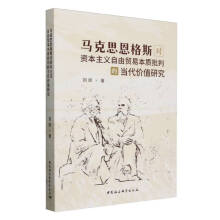《<资本论>的现代性维度研究》:
其次,康德对启蒙现代性的辩护,在于赋予启蒙新的目标——现代理性主义自觉,从而赋予现代性以道德理性的精神内核。
在卢梭看来,启蒙理性使一切都私人化了,这种私人化的理性自由若没有社会契约的束缚,那么人终将会堕落为恶。所以,卢梭一方面要煞费苦心地为社会制定完美的立法,一方面,却又对人性的腐化和堕落忧心忡忡。他感慨要为一个国家制定一套完美的律法,简直是非得先有一群天使般的人民才可以。但是康德却并不这么认为,康德认为,为国家立法并不需要一群天使般的人民,哪怕是一群魔鬼,只要他们拥有如此的智慧也是可以的。何况在这个社会中,并不是一群魔鬼,而是一群自由的,一群本性中即使存在着恶,但却仍然具有善良意志的人民。可以说,康德把启蒙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人类要脱离自己不成熟的状态,并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从而使“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康德本人曾明确说过他自己的思想来源于两个人,一个是牛顿,一个便是卢梭。但是,在对理性的理解上,康德与卢梭背道而驰。不同于卢梭所认为的理性使一切都私人化,康德赋予理性以普遍的形式。
一方面,在启蒙理性的定义上,康德区分了“公开”运用理性与“私下”运用理性。启蒙所要求的自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唯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相对于“公开”,卢梭所说的理性的私人化实际上属于“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有限理性是狭隘的,甚至会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
另一方面,针对卢梭提出的幸福是源于自然状态下的本能,康德给予否定,并指出真正的幸福是源于理性的:“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而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他的幸福和美满”。人的理性是人全部自然禀赋得以充分发挥的必然,并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个人生命的短暂性,人们需要世代相继的启蒙来充分发挥自然禀赋所赋予的人的理性。在这个过程中,人自身必然会超脱出动物生存本能的生存机制,并因为具有理性而使其物种得以存续并将自身禀赋充分地发展。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文明存续与发展的意义上获得成熟的幸福。
第3,对于卢梭批判启蒙过程中人性中展现出来的“堕落”的部分,康德辩证地给予了肯定。康德引述了圣经中的故事,人类吃了禁果懂得了善与恶,所以便从天堂堕落下来。既然人是自由的,所以恶便是人类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一环。人性中非社会的本性,亦即自私化的倾向会驱使人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但是在这种虚荣、权利和贪婪的驱使下,按照卢梭的理解,也唤醒了人类才智等自身的全部能力,从而使他们迈出了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第一步。如果人类没有这种非社会性的驱动力,康德称其为“并不可爱的性质”,那么人类的才智不会发展,人类的价值就将跟温顺的家畜没有区别,人类将永远被埋没在原始社会形态的胚胎里。
既然“大自然在要求纷争不和”,那么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在人性必然是存在恶的前提下,在人类步入社会性的条件下,不至于使人类堕落到相互反对的状态当中?这就又回到了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如何解决卢梭提出的资产者的个体性与普遍性利益之间的对立,从而实现从个体自由到普遍的自由的转变,进而实现普遍自由问题。康德认为解决这一现代性问题的关键离不开启蒙。启蒙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病态的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康德对启蒙的一个重要肯定,那就是启蒙的作用,就在于去自然化,并在启蒙的理性实践中,为道德的善铺就道路。他承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道德上的恶有着一种与他的本性分不开的特点,那就是它在它的目标上(尤其是在对其他同样意图的人的关系上)是自己违反自己并且要毁灭自己的,于是这就为(道德的)善的原则准备了道路,尽管还要经历漫长的进步。”
从霍布斯到卢梭,启蒙政治经历了从自利主义到道德普遍主义的演进,卢梭率先批判了启蒙的利己主义并开辟道德政治的新领域。康德洞见到了卢梭政治理论中蕴含的道德维度,但也意识到卢梭政治理论中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极易使卢梭的道德政治激进为一种过度抽空了自身并沦为吞噬一切异质性的道德恐怖。为了避免这种抽象的普遍性的绝对自由所造成的恐怖,康德先验伦理学将理性的普遍性限制了在道德事务的领域内,希望通过树立理性的权威,为现代社会构建道德基础。继承卢梭“公意”的立法原则,康德从人的善良意志出发,探讨了为“公意”立法的道德形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