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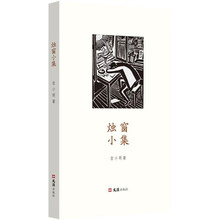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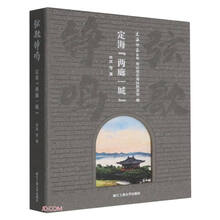

25年前,走在野草缠脚的三宝小路,仍可听见的十几架水碓的声响,粉碎着三宝瓷谷一片的瓷石,也不尽地分割晨昏:冬天雨水很少,晚上听过去,缓慢的“砰咯、砰咯”声,非常孤独,像失双的白鹭;一场春雨过后,“哐切哐、哐切哐”,任性,纵情,似有思春的呐喊。还有,枝头上雨点一样洒落的鸟叫声,撕开晨雾升起炊烟的鸡鸣声,偶有村民经过的打趣声、哗然声,稻田里有轻风拂过的沙沙声……这一切混沌、刷满岁月“包浆”的声音,敲窗过耳,让李见深白日神智清明,夜里睡得深沉。早上醒来,不像他在国外国内许多地方打开双眼,神志有些恍惚:我这是在哪里?
花一万美元,在三宝谷里买下一块叫“四家里”的地方,原本是一个荒芜已久、建筑倾塌的村子,只有几个老人寡妇守节般存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个梦,宛若一朵云,从公元四世纪飘到今天,此后中国的文人大多在形而上的这块云里徜徉。当这块云飘到这代文化人的时间段,同为柴桑孑遗的他,不仅是心念神往,还想让这朵云形而下,化作一滴滴雨水,落在三宝,让三宝做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真正走得进去的世外桃源。
——胡平《“老神仙”小传》
如今我们尝试换用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在生命面前,人与物是可以平等的。这种表述,只是人类本性对未来或未知的一次小小让步,是喊出尊重其他物种的一个口号,尚且算不上一次行动。一个科学家可以说自己已经将一种生物的习性、它的生老病死已经研究透彻了,甚至可以用克隆的技术,将它完整地复制出来。只是这样真的就算完全了解了吗?借用惠子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它不是诡辩,而是附加了一种更加高尚的人性因素,或者说,超人性的因素,去凝视宇宙间的一草一木。一种更加接近万物平等的凝视的目光。
将讨论一条狗的话题,提升到这种高度,似乎暂且没有这个必要,但要用人性来概括那条狗给我带来的感受,又感觉不妥。它的眼神里,确实有一些非常尖锐凌厉的东西,但不是兽性。它早已丧失了一条狗的警惕和敏捷,显得慵懒与无所谓。那更像是一种平静的深邃。就像时光不断地打磨,将一颗宝石粗杂的表皮去掉,只剩下纯净无瑕的内在。不论外界再如何侵蚀,依然难掩它的光泽。
——李路平《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