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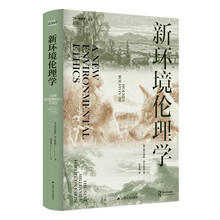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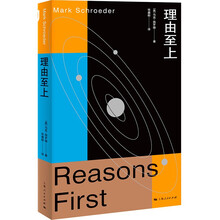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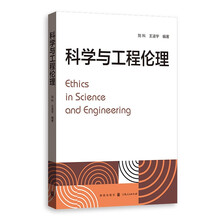




女性主义理论巨匠、波伏娃之后法国女性主义代表人物
作者伊利格瑞多与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西苏(Hélène Cixous)并称为当代“法国女性主义三巨头”(holy trinity)。她被巴特勒誉为“可能是我所阅读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中最精通哲学之人”。她的作品极其原创性与批判性,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女性主义学者。
“性差异”作为两性解放的重要动力
20世纪以来,以人权、平等为根基的妇女解放运动硕果累累,伊利格瑞一方面持续关怀两性平权,另一方面着重思考差异的可能性。她深信女性身体之独特性;坚持从本体层面思考性差异,以此推翻传统哲学对“同一逻辑”的预设。本书不仅体现了她广博深厚的理论功底,还展露出她勇于挑战父权传统的基进本色。
新爱欲伦理的重要读本
伊利格瑞在书中倡导一种进步的爱欲伦理:两个主体是对等的,没有缩减同化、占有控制。爱之中的男人女人朝向彼此,通过丰饶的肉身之爱,焕发神性与美。
知名学者张念倾情翻译并作专文导读
译文精心打磨,语言优美流畅,极力还原伊利格瑞诗意动人的写作风格。
封面再现欧姬芙名作、新锐设计师汐和操刀
幸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授权,封面画作为美国现代艺术大师乔治娅▪欧姬芙(Georgia O'Keeffe)名作《黑色鸢尾花》,以此映照伊利格瑞笔下理想的亲密爱侣:在轻抚和缠绕中以“二”去爱。小32开瘦长本精巧便携,护封特选绵柔艺术纸,尽享柔软舒适的阅读体验。
节选自
他者之爱
和世界相关、和它的时空相关
栖居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属性。哪怕这属性是无意识的,不完满的,尤其在伦理维度上,男人总是到处搜寻、建造、营造他自己的家:岩洞、棚屋、女人、城市、语言、观念、理论等等。
感知—这是女人的一般维度吗?女人好像还停留在知觉之中,没有命名或者概念的需求,没有封闭自己。停留在知觉之中,意味着总在开放性之中游荡,与外面,与世界相适应。感官警觉,女人有时会忠于世界吗?没有必要分享,在两种光亮、两种黑夜之间。去感受,停靠在感觉的世界而不是去关闭它,关闭自身,在世界的边缘去构造、去观察。用改变去回应时代、回应时间、回应空间。最困难的就是在空间之中建造记忆,在那里,男人有时会在悲痛记忆中关闭自己,沉溺于怀旧,遗忘槛界,遗忘肉身。
那些记住的和遗忘的悲痛。寻找那些被抹除的,或那些无法抹除已经被铭刻的。忧惧重复、再生产,忧惧那些被抹除的会再来。通过语言,一种双重的天性或反抗的天性正在发生。
重复也许能够峰回路转,接续,(通向)更好的道路。这也许是可悲的,紧急的,唤起一些事物,那些失去根基、正在死去的事物回来了,没完没了,因为缺乏生长的元气。
记忆病理学也是历史病理学。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压抑“那些地底下的诸神”是不可能的,除了死亡和回归,我们不能够抹除生命的根基。
哪怕作为男人,有意无意地为了活、生存,为了栖居和工作,供养和盘剥母性—女人,他遗忘他者,遗忘了自己的生成性。他阻止生长和重复,无休止地寻找记忆和遗忘割裂的时刻,这是他失落的时刻。但是,越是重复,越是把自己裹在封套里,裹在容器里,裹在“房子里”,这些事物统统都在妨碍他发现他者,发现自己。总是感怀那最初的和最后的逗留,因而阻止他去和他者相遇,和他者共同生活在一起。怀旧锁住了伦理世界的槛界。为了栖居,为了收容他者,摆弄起顺手的金钱工具。但金钱不能支撑起生活。相应地,金钱无法取代生活。金钱无法购买处女地,一种别样的创造力,为创造所提供的支撑、滋养、空间和材料,这别样的创造—男人或女人—报之以需要和欲求:建造一种身份,一种语言,一种劳作。
性态和技术
性倒错往往被奉为摆脱压迫性道德的手段,但依然臣服于性差异的道德,这一传统运作的等级制,经由技术世界,会运行得更好或更糟。如今,撕裂的身体如同机械身体一般。能量等同于工作能量。这些成了我们时代无所疑虑的部分并达成了共谋,进步虽然是明显的,但这完全遗忘和回避了肉身。
工作竞争和性活动的竞争是共犯,殚精竭虑的工作和性高潮的放松是共谋。同一个身体卷入其中,和符号保持同样的关系,肉身在此无关紧要。“世界”操控着经济游戏,却并未掌控主体意图及其与他者的相遇。世界操控一切。创造者对他所创造的唯命是从……不再具有意志和意愿。男人创造的世界已经不宜居住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一个不宜栖居的功能性身体?正如技术和科学。或科学的和技术的世界。
这样一来,生殖的性态被某些男人或女人所轻视或吹毛求疵也就不足为怪了。“部分”的性态依然臣服于技术。不管是善意的还是病态的。
部分的性态在“技术”地触摸、呼吸、聆听、观看和品味,这些预先制造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热衷于技术手段。为了适应这些,身体被不同的感知速度撕扯。身体总是功能化的,根据这不同的感知度。但前提是大地的或元素性的东西总会把它聚拢。
如今,人和机器差不多了,他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设想成机器:性的驱力,被收缩和释放所控制,或好或坏的运作秩序,等等。一种能够统一不同驱力的事物被遗忘了,它和爱相关吗?爱的思想?爱赋予一种有机的节律,爱能获取和赠予时间。朝向生产性,竞赛才能获得平静和喘息之地,性行为也是这样的。那些抵制肉身离散、流离和炸裂的事物,那些抵制道成肉身的事物。尼采认为主体是一颗原子。如果没有找到生命提升的节律,这原子就会破裂。犹如植物的生长机制,但又和植物生存截然相反。如果在科学和技术论时代,男人把自己设想成一台机器或一台原子机器—在生物学、医药学、心理学、语言理论这些话语中就能看到—那他就应该扪心自问至少两三个问题,关于存活、关于存活的普遍性。
存活?
一个我们常常能听到的词汇,是我们这代人的通关词,无力思考、无力创造、无力自为地去活,统统称之为存活。
存活还有意义吗?我们给出的意义完全是反尼采主义的,然而这词的用法来自尼采和他的“信徒”。在尼采那里,存活是指活出更多,而不是赖活着。存活是指把握生活的风格,这样一个人就能去发现和创造新的价值。活着是桥,抵临超人,在人之外开发人。
活着,在很多地方、很多对话中意味着休眠。等待,等待什么?这种存活、这种对活着的解释,或多或少耗尽了那些力图去生活的事物和存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存活变成了小布尔乔亚营生了吗?在西方,这些似乎都是常规问题的缺失:关于超验,关于上帝,关于无限性所带来的经验悖论。
为了“自愿地”舒展,除非回到身体—肉身价值(这价值还未绽放),还有谁或什么能够将我们带出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状态?因为男人从来无法承担道成肉身的伟大节律,呼吸,血的循环这类事情。他拒绝生长,为了成熟退回孩提时代。他斩断与女人—母亲的脐带,母性依然在为他呼吸、喂养他、温暖他,给他一个家、一个巢。生命在子宫中延续,正如高科技世界的对位法,在这里男人依然像个婴儿,失语,正如他和母亲相关?
如果想要永久独立和自由地掌控生活,男人就应该建立起一个空间,一个性差异的时—空。他不再包裹自己,不再被母性所看护,一方面,他不再将女性当作玩具和机器人,另一方面,无论怎样肉体都应该在场?如果有肉身,自主的呼吸就会充盈身体。贯通爱与生命的自主形式。存活轭住世界的终结、男人的旧时代,怀抱中的婴儿心态,无法满足他自己婴儿般的需求和欲求。是一种在母亲看照下的寄生虫,但无论如何,是寄生虫在统领这世界?
如果男人—他们宣称的是人性—要摆脱存活,他须摆脱婴儿和旧式男人的混合体,这依然如故的处境。我一直认为,医疗保健效用的提高仅仅缓解了这样的心态。鉴于类似的或互补性风险,还有战争的胁迫。成年人的恐怖游戏和孩子们的游戏没有区别(孩子们玩枪弄棒,像成年人那样扮演战士,是否可以这样说,成年人不也正像个孩子吗?)
若想从母性支撑状态,从全能大他者—可推断为上帝—达到成熟,他将会发现有些东西为女人所固有,当然不是指母性?另一个身体?另一种机器?(在最坏的程度上?)具有完全不同能量?这会让男人—人类—瞥上一眼的某种东西。不是他的世界,也不是遵从他的说明书建造的。
这需要男人先停止对女人的设定:
—再生产,作为生育机器,居家的,还要打扫庭除,提供食物,等等。
—死亡监护,炉边保育员,欲望的童贞女,如某种符号—身体的无言子宫,男人的心灵(尤其是物恋?)
—做爱用的机器玩偶,仅存诱惑、死气沉沉。这情感不是“她自己的”,而是为了他人,也为自身驱逐她。女人的诱惑被人们滥用了,诱惑并非为了她或她们自己。这诱惑让女人从自在之中连根拔起—正如黑格尔所说—转入为他状态,将她带离生机勃勃的生命,这并非一无是处,这样一来,她就被分派到一种公共效能(尽管这是一种私人性的操演),仅仅是为了维持公共机器的运转。
—成为男人或人类的道成肉身,幻想的道成肉身;她是铭刻的基地,多多少少像尊活雕塑,阴森森地围绕在乡村、女神或垃圾堆的周围。
也许男人会发现在女人那里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些东西存活着。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孩子,没这么简单的。一些别的事别的人。面对这不同,他一无所知?或者,让那些事物屈从于他的理念,这样一来他失去了他的权力吗?这想法太过不同,他甚至对此从来没有认知?哪怕在性活动中?他依然采用这样的术语:
—勃起;
—狂喜,在自身之外(在大他者之中?);
—射精,在自身之外进入他者。
男人或人类如果想开创某些富有生机的事物,他就应该采纳新的生命契约,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不是男人曾设想过的那些:自在、自为、为他。而是在女人那里某种固有的居间位置?
译者导读
英译者前言
前言
Ⅰ
性差异
女祭司的爱欲:读柏拉图《会饮篇》,“狄欧蒂玛的话”
空间,间距: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Ⅱ
自爱
惊奇:读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
封套:读斯宾诺莎《伦理学》,“论神”
III
同一之爱 他者之爱
性差异的伦理学
IV
他者之爱
不可见的肉身:读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这交错—这交织”
丰饶的爱抚:读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爱欲现象学”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