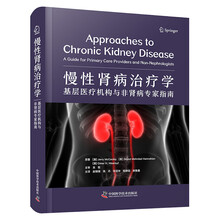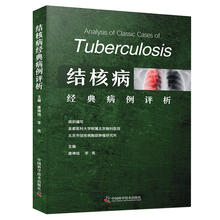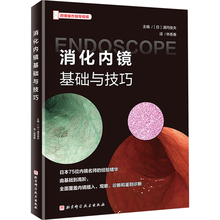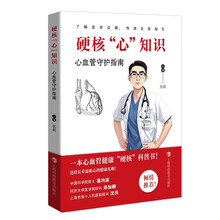第一章肠道微生态概述
第一节肠道微生态
人体肠道微生态是指人体肠道中栖息的微生物的总称,目前的研究以细菌为主,还包括古菌( archaea)、病毒、真菌和原生生物及其代谢物。以上微生物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并通过相互接触、分泌蛋白或代谢产物与宿主形成复杂的互作网络,构成平衡的微生态系统。因此,该系统与人体健康和疾病发生息息相关。已有研究显示,肠道微生态与人类各种慢性疾病有关,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脑部疾病和肿瘤。肠道微生态在维持人体健康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肠道微生物组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
一、什么是肠道微生态
人体的微生态系统存在于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和皮肤等多个部位,其中肠道微生态作为消化道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机体众多生理、病理过程。寄生于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众多,包含了细菌、病毒、真菌、古菌等。寄生于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与人体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肠道微生态系统。肠道微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肠道菌群、肠黏膜上皮组织和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它们共同组成了肠道的黏膜屏障,而肠道菌群在其中发挥了昀重要的作用。它们和人体是一种紧密共生的关系,至少,离开了肠道微生物的作用,人体是无法独立生存的。例如,人体必需却又无法自身合成的维生素 K,无法通过食物直接获取,只有通过肠道细菌的代谢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
肠道微生态与人体其他部分的健康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其与人体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沟通”,研究者称其为轴。随着“肠 -肝”轴、“肠-肾”轴、“肠-脑”轴、“肠-肺”轴、“肠-心”轴、“肠-骨”,甚至“肠-肝-脑”轴等众多轴逐渐被研究者提出,肠道微生态在人类健康和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地位被愈发重视。
肠道微生态对宿主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宿主与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也是宿主免疫耐受所必需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态的紊乱可能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密切相关,包括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等。关于肠道微生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假说,目前尚无成熟定论。多数研究表明,肠道细菌分泌的小分子物质可通过黏膜表面的转运体或内吞作用进入细胞,激活一系列与细胞生存相关的细胞通路,如细胞膜表面转运体相关蛋白的基因异常表达与结直肠癌、炎性肠病等的发生相关 [1]。Toll样受体( Toll-like receptors,TLRs)属于固有免疫系统的模式识别受体,正常状态下 TLRs识别细菌的脂多糖( LPS)和鞭毛、病毒核酸及真菌的酵母聚糖等外界抗原,如 TLRs7识别单链 RNA,TLRs9识别双链 DNA,而 TLRs4则识别脂多糖。自发生发中心的 B细胞和滤泡 Th细胞合成高亲和力的自身抗体,自发生发中心的形成受到 B细胞表达固有 TLRs7和 TLRs9的调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 TLRs7、TLRs9表达水平增加,且与 IL-6、INF-γ及 TNF-α等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炎性因子水平相关 [2]。也有研究表明,细菌或病毒的双链 DNA通过TLRs9导致自身免疫性的 B细胞激活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复发相关 [3]。分子模拟学说为微生物诱导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机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例如,在小鼠中,某些细菌的 DNA及细胞壁成分可诱导抗双链 DNA抗体的产生[4]。既往研究验证,抗双链 DNA抗体可特异性结合纯化的伯克氏菌抗原,这种表位模拟可能解释了伯克氏菌的感染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症状加重的原因 [5]。肠道细菌多样性的下降是肠道生态紊乱的重要标志。此外,肠道生态紊乱的概念亦包括如拟杆菌和产丁酸细菌等益生菌的减少,以及大肠杆菌在内的变形杆菌门等在内的致病微生物的增加。这种肠道微生态失调可造成免疫系统的缺陷,进而导致免疫介导疾病的发生 [6]。
近年随着对肠道微生态的深入研究,发现古菌是肠道微生物的另一个重要组成成分[7]。古菌又称古细菌、太古菌或太古生物等,是原核生物中的一大类,被认为是与细菌、真菌、病毒平行进化的一类微生物 [8]。有研究发现,人和单胃动物体内存在部分古菌,在超过半数的人肠道内均可检测到古菌的存在 [9]。因此,古菌成为近年 IBD微生态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肠道微生态研究历程
微生态领域在近 70年间发展迅速, 2019年 Nature Milestones专题报道了微生态研究中从 1944~2019年 23个时间节点的 25个里程碑式研究,可以发现关于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占据多数(图 1-1)。
图 1-1 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历程
微生态研究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现代的领域,但是昀早的观点可追溯到 17世纪七八十年代。1683年,列文虎克通过比较自己和他人口腔中的菌群,发现 5种不同的细菌;而后通过比较口腔与粪便中的微生物群,列文虎克提出不同身体部位之间、同一部位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微生物群存在差异。
1853年约瑟夫 莱迪的专著 A flora and fauna with living animals被认为是微生态研究的起源。随后,一批科学家为这一理论的丰富贡献了力量,包括巴斯德支持非致病微生物对人体至关重要,并提出细菌治病的理论;梅契尼可夫指出,人体内微生物的组成及其相互作用能对健康个体产生重大影响;埃舍里希则认为研究内源菌群是理解消化生理学、肠道疾病的治疗基础。
1890年,Goch提出假设并尝试建立微生物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标准,但是由于当时的实验技术的限制,大多数肠道微生物无法被研究。 1917年,德国医生首次分离出大肠杆菌 Nissle 1917菌株,如今这个菌株仍是常用益生菌的来源。 1944年,厌氧菌培养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主要归功于亨盖特开创性的工作,该方法沿用至今,被称为“匈牙利技术”。1958年,Eiseman等报道了使用粪便灌肠成功治疗假膜性结肠炎案例,这种治疗方法被广泛接受并作为复发性艰难梭菌相关性感染( CDI)的治疗方案。 1965年,Scheadler及其同事将细菌培养物转移到无菌小鼠体内,通过转移实验关注肠道微生物对宿主的影响,为肠道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1972年,Peppercorn和 Goldman发现抗炎药物柳氮磺嘧啶可以在常规大鼠和人类肠道细菌培养时降解,但是在无菌大鼠体内无法降解,提示我们肠道微生物群在药物转化中发挥作用。 1981年,多项研究同时表明,肠道微生态在胎儿肠道发育完成后不久即开始建立,并与产道分娩、母乳喂养等相关,而这些微生物在婴儿出生后的免疫、内分泌、代谢等各系统发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96年,基于 16S rRNA测序方法来评估微生物的多样性,解决了无法纯化培养的难题,而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加入,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微生态研究的发展。 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测定 16个成人粪便样本发现,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微生物群落,并且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稳定,这项研究为日后回答个体间微生物系统差异、微生物群稳态以及什么是正常微生态组成等问题提供了基础。
进入 21世纪后,关于肠道微生态的研究突飞猛进。 2003年,Forest团队研发出一种快速且无偏见的随机鸟枪法测序,用于分析单一噬菌体基因组 DNA。而后,随着宏基因组学在此技术基础上拥有了更强的解析能力,人类在粪便样本中获得了*个未被培养的病毒,细菌之外的微生物与宿主的联系也变得愈发清晰。 2006年,两项里程碑式的研究诞生,表明微生物群的转移能够转移宿主的表型,也揭示了改变宿主饮食能够对肠道及其他器官中微生物的构成和行为产生动态影响,从此疾病预防及治疗拥有了全新的思路。2007年,定植抗性机制被阐明,对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及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了重要参考。同年, Eline团队利用“组学技术”对人体功能微生物群进行体内分析,补充了分类学以外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微生物信息的多样性。
近十年来的研究在此前的基础上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认识肠道微生态。 2010年,在使用抗生素治疗的病人的粪便中发现,药物影响 1/3的细菌类群,包括物种丰度、多样性及均匀性。尽管多数细菌群体在治疗后恢复,但仍有个别分类群体的丰度无法恢复原样。同时,该研究还指出,同一个体在两次治疗中,微生物群落的改变没有相关性。同年,生物信息学的广泛应用使得微生物组测序数据得到更深入的挖掘。2011年,一项大型人群的微生物组分析结果被发布,大量数据的分析促进了我们对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明确了微生物对人类健康及疾病之间的潜在关系。2012年,全球人类微生物组的结果公布,研究结果发现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同队列样本间,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也存在差异。同年,“微生物-肠-脑”轴被提出,揭示了肠道菌群与生活质量、神经活性代谢物相关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2013年,研究发现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SCFA)能够诱导调节 T细胞生物合成,揭示了这些共生微生物群体将以化学介质的方式影响和改变宿主的免疫过程。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微生物群是新抗生素的潜在来源,次年,研究发现靶向宿主的药物影响微生物群落,提示非抗生素促进抗生素耐药性的潜在风险应当被重视,同时给予我们一个指向性的信号:药物 -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及其副作用控制应考虑更多的维度——肠道微生态。2018年,研究发现人类微生物组影响癌症治疗效果,表明肠道微生物具有潜在“操纵”宿主生物功能的能力。2019年,组装得到的宏基因组提供了人类相关微生物群前所未有的特征,该方法应用于不同人体部位的数千种尚未培养纯化的细菌物种,大大扩展了已知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细菌系统发育进化关系。
随着一项项里程碑式研究成果问世,相信有更多的微生态成果将被成功转化至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编写:戴世学)(资料整理:廖威宏张杰鑫曹宇辰)
第二节肠道微生态的相关要素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病因未明、在免疫失调的背景下启动肠道菌群免疫应答所导致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 Crohn’s disease,CD)。目前观点认为,IBD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并且因免疫功能紊乱,肠道黏膜免疫对肠道菌群的免疫耐受水平下调,过度的免疫反应进一步加重了肠道微生态失衡,IBD与肠道微生态的此种关系,也是肠道微生态研究成果实现临床转化、应用的起点。因此,近年来随着 IBD致病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IBD的治疗方法在不断优化,除了免疫抑制剂、激素、抗生素等药物和手术治疗外,新兴的微生态治疗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图 1-2)。大量的案例和临床研究已经展示了微生态治疗,包括益生菌等生物制剂治疗和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等新兴疗法,以及在治疗 IBD上的应用前景。微生态治疗通过优化肠道菌群结构促进共生菌的增殖与干预有害菌在肠道黏膜的定植,以发挥共生菌修复肠黏膜屏障、杀灭有害菌、降低免疫效应水平、预防机会性感染的作用,昀终达到以非药物手段缓解患者症状、改善肠道功能的目的。此外,微生态疗法与传统疗法相比,有着副作用相对较少、原料来源广、使用便捷等优点,因此也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图 1-2 炎症性肠病传统疗法与新兴疗法概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