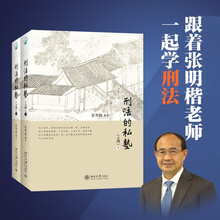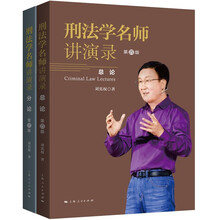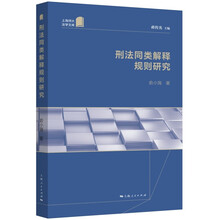出版说明
刑法分则是对具体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系统性规定,是我国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刑法分则对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刑法理论上,刑法学的重心就在于刑法解释学,而无论是从刑法中分则内容的比重还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来看,对刑法分则的解释、适用都应属于重中之重。
然而,一直以来,刑法学界偏重研究刑法总则,而轻视甚至不屑于研究刑法分则。现有的研究刑法分则的书籍,虽然看起来颇具规模,但基本上属于局限于对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之间的区别或者界限进行抽象讨论的教科书式的书籍。这类书籍没有问题意识,缺乏实例分析,或者主要是对司法解释规定的简单堆砌,既难以促进刑法分则理论的进步,亦无法为实务操作提供支持。
应当承认,目前市面上其实少有值得阅读、方便学习的研究刑法,尤其是研究刑法分则的书籍。学界所谓的研究,基本上限于抽象的、文献的、脱离司法实践的纯理论性的研究,对司法实践助益不足。可以说,实务人士很难找到能够真正为他们答疑解惑、值得他们阅读的刑法书籍。
自2009年从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以来,我始终致力于对刑法分则的研究,先后撰写并发表了一百多篇研究刑法分则的论文,出版了《公共危险犯解释论与判例研究》《人身犯罪解释论与判例研究》《财产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研究》《贪污贿赂渎职罪解释论与判例研究》《职务犯罪罪名精释与案例百选》,并且在校内外经常讲授刑法分则课程和做以刑法分则为主题的讲座。应该说,我对刑法分则有着相当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是我近十几年来有关刑法分则的思考、研究心得的集大成之作。
有关本书的内容,首先要略作说明的是,为使本书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同时也是出于篇幅的考量,我精选了实践中常用的重点罪名作为精解对象。为了更准确地厘定罪名的范围,我广泛征求了公、检、法、司、监等实务界数十位朋友的意见,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这一百个常用罪名。
本书写作的宗旨就是满足高校学生与实务人士研习刑法分则,领悟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以便更为准确地理解、适用刑法分则的需要。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书在写作形式上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实用性三大特色:一则,以法条为切入,条分缕析。本书综合运用刑法解释方法,系统地梳理了刑法分则中常用重点罪名的构成要件及其界限关系。二则,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本书采取“问答法”,在各罪条文之后直接列出相应罪名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总计1300余问,并予以解答,以求重点问题重点解决,尽可能激发读者的问题意识。三则,以案例为线索,贯通理论与实践。在对各罪疑难问题的解答中,本书结合逾300则实践中的典型、疑难案例,用以举例论证,并对部分重要判决进行评析,以使读者充分了解本国实践中的问题,争取为读者解决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对各罪名构成要件、保护法益、犯罪类型、犯罪特殊形态、罪数、追诉时效等适用上的疑难、复杂问题的精解,以及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解读与反思。
对罪名构成要件的准确解释是适用刑法分则条文的基础,是司法工作人员正确认定犯罪的前提。本书主要是对常用百罪构成要件的全面精解。例如,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本书认为,《刑法》第114条、第115条中的“公共”的含义是不特定且多数的人,除此之外,“公共”一般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再如,关于职务侵占罪中职务侵占行为是否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窃取、骗取行为,本书认为,职务侵占行为只能包括侵吞一种情形,即将自己基于职务或者业务而占有的本单位所有的财物占为己有或者使第三者所有,不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除非《刑法》有特别规定(如《刑法》第183条第1款)。又如,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根据《刑法》第240条第2款之规定,认为本罪的实行行为是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这六种行为之一,但本书认为,对实行行为只能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和法益进行具体确定,与其他出售类犯罪一样,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一种,其他的只是预备或者帮助行为。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要对具体犯罪作出实质合理的解释,必须对法益有准确的理解。本书对各罪的解读亦建立在对其法益的深刻理解之上。例如,关于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本书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该罪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说明高空抛物行为主要侵害的不是公共安全,而是有关公民头顶上的安全的公共场所秩序,所以不需要所抛掷的物品具有致人死伤的可能性,只要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破坏公众生活的安宁,就可能构成本罪。再如,关于毒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但这种抽象性的表述并不能说明毒品犯罪的处罚范围,亦不能在对毒品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方面起到指导作用,甚至导致对某些毒品犯罪既遂的认定过于提前,故应当认为,毒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健康。又如,关于贪污罪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应当认为,贪污罪侵犯的主要法益还是财产,其次才是所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受贿罪是侵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犯罪,是亵渎职务的犯罪,是典型的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可见,二者的罪质存在本质的不同,不能将贿赂犯罪作为财产犯罪进行理解和认定。
犯罪类型对于认识犯罪、适用法条、考察犯罪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犯罪进行分类一定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否则就纯属学者的游戏。本书在探讨具体罪名时,特别注意研究犯罪类型及其对罪名解释、适用的影响。例如,本书认为,介于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之间,还存在一个独立的危险犯类型―――准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条文中的“危及”“足以”表述,不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志,而是准抽象危险犯的标志。对于准抽象危险犯,在认定具备一定行为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有无危险的具体判断,但又不需要达到存在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的程度。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罪,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污染环境罪等皆在此列。再如,本书认为,结果犯是与行为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并且对因果关系不需要作特别判断的是行为犯,而行为与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一定的时空间隔,因而需要以因果关系作特别判断的是结果犯。而实害犯是与危险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实害犯是以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为成立条件的犯罪,所以只有过失犯和滥用职权罪等部分故意犯罪才是实害犯。又如,继续犯与状态犯的区分关系到追诉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当扩大了继续犯的范围。本书认为,区分继续犯与状态犯,应从实质上进行判断。只有能够肯定法益每时每刻都受到同等程度的侵害,能够持续性地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才能认为是继续犯(持续犯),否则只能认为是状态犯。此外,通常只有侵害或者威胁人身权益的犯罪,如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危险驾驶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才可能被认定为继续犯。
众所周知,由于刑法分则并未规定对于哪些犯罪应当处罚其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所以,必须对具体故意犯罪的可罚性进行实质判断。本书除了对基本犯的特殊形态进行讲解,还特别重视探讨加重犯的特殊形态问题。例如,对于“二人以上轮奸”,本书认为,其相当于量刑规则,并非加重的犯罪构成,只有成立不成立的问题,没有未遂、预备与中止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人以上完成强奸的,成立轮奸,适用轮奸的法定刑;实际上没有两人以上完成强奸的,不成立轮奸,按照强奸罪的基本犯处理。再如,关于“抢劫数额巨大”的未遂问题,本书认为,行为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抢劫目标,客观上也已经接近数额巨大的财物,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无论是未抢得财物,还是仅抢劫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均成立抢劫数额巨大的未遂,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法定刑,同时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又如,本书认为,多次盗窃不以每次盗窃既遂为前提。成立多次盗窃,也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盗窃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反过来说,如果盗窃数额较大既遂的,不应评价为多“次”盗窃,而应单独评价。我国刑法规定多次盗窃,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不处罚数额较大的未遂,但行为人多次盗窃未遂的,无论违法性还是有责性,都较重,值得科处刑罚;二是一般只有数额较大的财物才是盗窃罪的对象,但行为人多次以一定价值的财物(不是价值低廉的财物)为目标进行盗窃,事实上也盗得一定价值的财物的,由于是多次实施,所以无论从违法性、有责性,还是预防犯罪的必要性看,都应科处刑罚。所以,多次盗窃应限于两种情形:一是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而未遂的,二是以一定价值的财物为目标盗窃既遂的。也就是说,若既不是数额较大的未遂,也不是以一定价值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既遂,就不能被认定为多次盗窃中的“次”。既然把多“次”盗窃限定为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未遂和以一定价值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既遂,就应认为“多次盗窃”相当于量刑规则,只有成不成立的问题,而没有未遂与中止的问题。
正确认定罪数,是准确定罪、合理量刑、实现罪刑均衡的前提条件。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一直以来都固守“互斥论”,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普遍是一种对立排斥关系,因而总是孜孜不倦地探寻此罪与彼罪之间的所谓区别或者界限。本书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之间普遍不是对立排斥关系,而是一种包容竞合关系。例如,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故意杀人罪与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在于行为是否危害了公共安全,即:危害公共安全的,只能成立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危害公共安全的,才成立故意杀人罪。本书对这种“互斥论”存在疑问。假如甲向一公寓楼放火,现场发现有一个人死亡,但不能证明这个人的死亡是放火行为造成的,则因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只能认定成立放火罪,由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能适用《刑法》第114条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乙向独门独户的独居老人的房子放火,现场发现独居老人死亡,但也不能证明独居老人的死亡是放火行为造成的,则因为没有危害公共安全,成立故意杀人未遂,适用《刑法》第232条规定的基本犯法定刑并适用《刑法》总则关于未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完全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很显然,甲的行为的危害性重于乙的行为,处罚结果是前轻后重,明显失衡。因此,应当认为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是竞合关系,实施放火等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时,既成立放火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成立故意杀人罪,从一重处罚,也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认为有所谓交易关系存在的就成立强迫交易罪,没有交易关系存在的就成立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其实,即便存在所谓交易关系,也可能同时成立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或者敲诈勒索罪。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之间也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竞合关系,如果虐待行为可以被评价为伤害、杀人行为,行为人又具有伤害、杀人故意,是完全可能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除了上述对刑法分则条文内容的解析,本书还注重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审视与反思。无论是做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务,都绕不开最高司法机关就如何应用刑法分则条文所作出的解释,而司法解释也存在解释不当的现象。例如,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将“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解释为《刑法》第143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但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二档法定刑适用的条件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其他严重情节”应是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相当的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也就是说,该罪加重犯可谓自然犯、实害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金额大,只是说明抽象危险性程度高,而不能说明对公众健康实际造成的危害严重,所以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难言妥当。再如,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以及1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其“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通常标准的50%确定。本书认为,曾经受过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只是表明行为人再犯罪可能性较大即特殊预防必要性较大的预防要素,不是反映不法程度的责任要素,将预防要素作为责任要素,混淆了预防刑和责任刑情节,明显不当。又如,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25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本书认为,上述规定可能存在问题,因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加重犯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中的“重伤”肯定包括过失致人重伤。也就是说,过失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伤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犯论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故意重伤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本犯与故意(重)伤害罪数罪并罚,最重只能判处20年以下刑罚,明显罪刑不相适应。所以,对于故意重伤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也应当评价为“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伤”,适用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法定刑。
诚如西原春夫先生所言,“在刑法的这张脸上,包含着被害人的父母、兄弟的悲伤与愤怒,包含着对犯人的怜悯与体恤,也包含着对犯人将来的期望与祈盼;此外还一定包含着法官在充分理解犯人的犯罪动机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犯人科处刑罚的泪水”。刑法及其效应是复杂的,牵涉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重视刑法中的每一个罪名,使尽浑身解数,合理地解释、适用刑法分则条文。本书只谈具体的问题,不过多关注抽象的理论,应该更能契合实务人士的学习要求。希望本书有助于其提升业务能力,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进步;也希望读者在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的不断碰撞中深刻领略刑法分则解释的奥妙。当然,由于我的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亦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洪兵
2023年7月8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