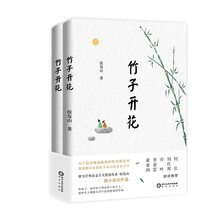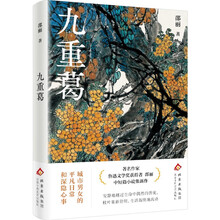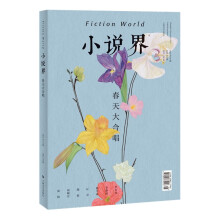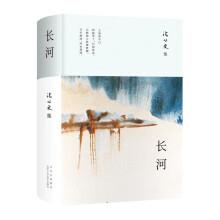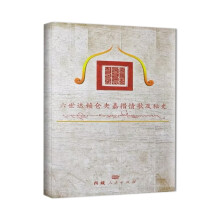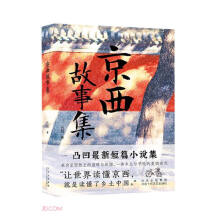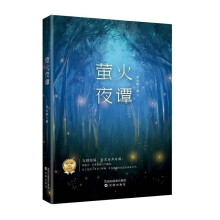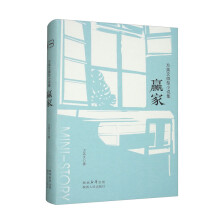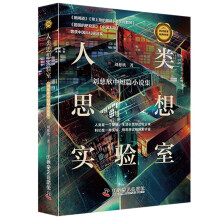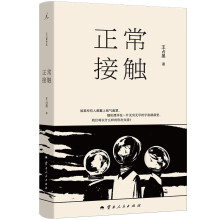大学
这里随处可见帝王将相的历史荣光。旧时宫阙的尘埃随风而逝,飘散在了黄河流域大平原。这里曾是传说中老子和孔子相会的地方,却没有留下任何古迹供人凭吊。洛阳城依旧坐落于河南省,春天的桑树依旧开满了花,龙门的壁立千仞仍然像以前那样,在南面守护着这座城市。白居易在这里留下了诗篇。无数佛窟的倒影荡漾在伊河的波涛中,千百尊弥勒佛俯瞰着过往的商旅。人们沿河上行,走进秦岭的余脉。
伊河两岸排开一片土地,延伸到无边无际的重峦叠嶂中。这里的土地长出新的作物,大块大块的,看着像碧绿色的红薯田,还有开着红色花朵的棉花田。
几百年来,人们在这一带伐木为炊,却没有重新种植林木。现在这些山丘都成了荒山秃岭,看起来灰头土脸。大地干旱,而旱灾好似轮回的恶魔一样蹂躏着这片土地。
农舍像这里的人一样一无所有。用泥土抹墙的四壁内,就一床一桌,加上一个上了漆的柜子。在祖先牌位上供着纸钱。门扇上用大红纸贴着喜庆的对联。对联上的字句传了一代又一代,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在过新年时才会被重新书写在纸上。
一条大路沿着伊河走出去一百七十余里。在那里,山势渐高,伊河也变得更加桀骜不驯。这里就坐落着一个叫“难路”的小县城。“难”意味着艰难坎坷,“路”就是道路。顾名思义,“难路”就是一条艰难之路,一条坎坷之路。这条大路钻进县城东门,融入没有铺就鹅卵石的小巷里弄中,然后还向前延伸一段,但在穿过西门后就消失了。再往后就只有通向北边、南边和西边的乡间小路和骡马便道了。
北门、南门、东门和西门都是泥土垒起来的厚重城关,彼此连着年久失修的城墙。城关保存尚好,但城墙却已经破败不堪。这样的城关,别说小口径火炮都能摧毁,就连面对机枪恐怕都够呛。
这里暂时还没人想到大炮。而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1943年,已经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七个年头。在后方,人们关心的还是和平时期过日子的问题:麦子、高粱、棉花和油菜,物价飞涨与高利贷,还有两年前的大旱灾和去年的小旱灾,以及今年秋天的蝗灾。人们曾经试图挥舞手巾驱赶蝗虫,但该如何对付旱灾呢?只能把腰带再扎紧些。抵挡日本人靠的是我们的士兵、城墙和可以逃命的山区。
这里的山峦高耸入云,轮廓沉静分明。这里重峦叠嶂中暗色的峡谷和清泉溪流属于我们,这里的土地也是我们的。无论是天界还是凡间的权力,都不能将这片土地从我们手中夺走。不过话说回来,这座城墙可指望不上什么。至于当兵的是否可靠,那还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货色。有一支部队就驻扎在县城前边,我们认识这支部队,看到他们喝玉米粥,在身上扒拉着找虱子。我们听见草鞋在校场上走正步,听见“一二三,向右转”的口令。我们也认识那些军官,腰扎皮带,脚蹬皮靴。是的,蒋介石的军队还活着。难道不是整个中国都在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对敌作战吗?难道不是每家农户都要给军队上缴整袋整袋的军粮吗?可那些再也没有返乡的新兵是怎么回事?屋里少了一袋面,少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儿子,这一切总该有个说法。所以我们相信,也就是大家总说的,相信政府,相信军队。于是,我们就只操心自己的日常生活。
对这座城市的居民而言,日子过得并不容易。要是麦子的价格一个季度涨了五倍,而学校老师的工资只翻了一番,那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只有那些通过囤积居奇和走私的商人发了财。他们笑容可掬,穿着厚实的大棉袍,像变戏法一样在穷乡僻壤的难路县城里营造出一种舒适惬意的气氛。
这座小县城,以及这里的山川河流,都坐落在静谧之中。当日军占领省城开封后,作为全省文教中心的河南大学及其数千师生,就逃到了这里。只要还有空置的地方,河南大学的师生就搬进去住。城西的一座庙,北门边上的临时木板房,一座邮局边上的土坯房,都被用作了宿舍。他们刚抵达这里的时候,还是见过世面的体面人,打着领带,穿着高跟鞋。但当鞋跟跑坏,领带撕裂之后,姑娘们就学着做布鞋,用布来纳鞋底子,就跟当地妇女穿的一样。男生们也穿上了士兵那种露出线头的军装制服。教授们则在先前日子好过时买的丝质长衫外,套上了蓝色的帆布外套。只有聪明的脑袋和儒雅的举止显示出他们的学究气质和卓尔不群。他们在这个被遗忘的山沟里落脚,将就着住了下来,但举止依旧从容。他们没有去抱怨丢失的大件物资、祖宅、图书馆、实验设备,以及战前的美好生活,但他们会因为日常生活的艰难而叹息,感叹自己不得不在草纸上抄写教科书,感叹教室墨水瓶里的墨水都会冻住,感叹只能啃黑馒头,却吃不到肉。
但是,大学运转如常。
通往难路县城的大路上铺着一层黄色的尘土,一前一后相隔几步走着两个男人。他们穿着轻便的布鞋。保持着同样且均匀的速度向前赶路。布鞋上沾满了泥土。年长些的男子肩上挑着一副结实的竹扁担,扁担的两头垂着油布包裹的货包。另一个男人身穿蓝色布长袍,一身轻松地走着。那件蓝袍就算沾满灰尘,也看得出是件新衣服。他身上最显眼的是那顶城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