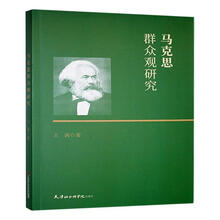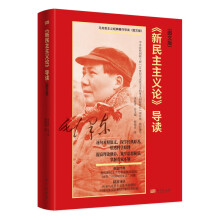《公正与人权: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价值与局限》:
三、“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正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对于哈贝马斯,正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合法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正义或代表正义的任何价值都只能是合法程序的产物。反之,任何没有通过合法程序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即非正义的。于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寻找或创制一种能够产生或保证正义的合法程序。在哈贝马斯那里,这种合法程序就是合理性交往,其典型形式就是不同交往主体之间的理性商谈。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经过理性商谈这种合法程序而形成的正义才可能是合法的、真正的正义。因此,哈贝马斯正义思想的主题与其说是正义,不如说是合法性。
哈贝马斯对合理性交往和理性商谈所内含的合法性意蕴的阐发和论证,来自他对历史上存在的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和纠偏,是对二者的综合吸收和扬弃创新。
自然法传统的合法性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并绵延至近代早期的契约论哲学。其基本观点是:“公正”“正义”和“理性”等是先在的、绝对的、普遍的,并与自然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一种无形力量的方式存在于政治共同体中,规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因而成为判断一种政治制度或法律规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客观标准。譬如,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可见,自然法传统的合法性是一个在形而上的、伦理学的基础上对现实制度和规范进行推演的结果,即政治合法性要借助于先验的伦理道德来进行自我辩护,这是合法性学说与价值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内在合流。但由于自然法的传统执着于对形而上的超验东西的追逐,因而不自觉地划出了一道它与人们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这就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它对社会现实合法性的解释力。特别是在传统形而上学遭到解构、统一的价值观发生分化的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若要以某种公认的道德观念来批判或维护现实政治制度或者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实证主义传统的合法性是由韦伯根据经验科学的方法和范式而开创的。其基本观点是:经验科学对诸如社会制度、统治秩序和法律规范等政治学、社会学问题的检验,只能在“事实性”“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的指导下进行,而不应当诉诸普遍性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因为它们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而与事实问题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从而是必须删除的。“就此而论,成为政治合法性准则的,一定不能是公正、正义、平等、自由等恒久不变的、符合自然理性的伦理要求,而只能是科学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的政治范畴。”而法律就是这种政治范畴的典型代表。这样,合法性就演变成为合法律性。
但是,对一种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而言,一旦它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删除任何有关价值关怀和道德规范的因素时,它也就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从而其合法性也就变得十分脆弱,因为“合法性的客观标准是被统治者方面的事实上承认”。另外,“合法性等于合法律性”也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可能成立,而无法超越阶级的局限性。例如,审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就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最接近于形式法合理统治模式的那种政治秩序,其本身并没有被感受为合法的;会这样感受的,充其量是那些从中得益的社会阶层以及它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家”。还有更为极端的例子,历史上出现的那些独裁政治和法西斯政权,都符合韦伯所界定的“规则合理性”“科学合理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等一系列法律形式,但它们决然不是正当的、合法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