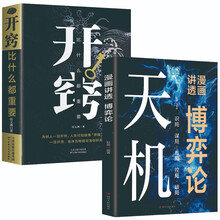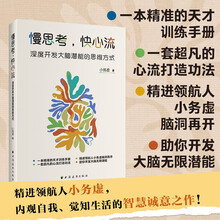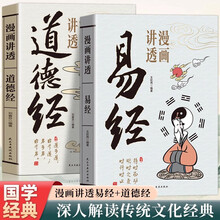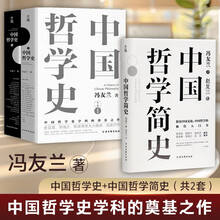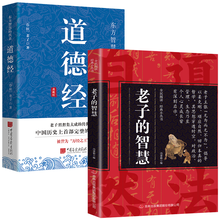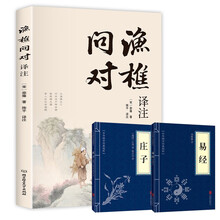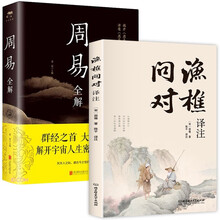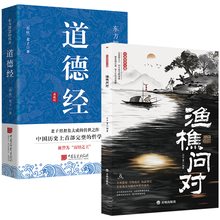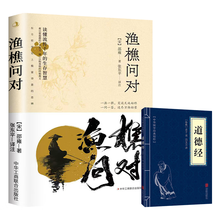自由的限度
庄子在《逍遥游》中借助大鹏描绘了一种豪放、浪漫的自由——“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表达了自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高远志向。
庄子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李白有诗云:“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这是超越神仙的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裴多菲的心中,自由是何等的珍贵。
古往今来,自由是多么令人向往,堪当“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无数仁人志士为自由而歌,为自由而搏,为自由而战。然而,无论我们把自由想象得多么美好,完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谁能一生自由,谁又拥有过绝对的自由呢?自由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诸如习俗、物质、时代、制度、法律、道德、组织、责任、能力等。
《礼记·曲礼上》中有言:“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避讳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要求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要“改读”或“换说”。因为避讳,也闹出许多典故和笑话。
五代十国时期,君主频繁更替,但有个铁打的宰相——冯道,关于他的名字有一个笑话。有一天,冯道命门客给他讲《道德经》,而书中开篇第一句便是“道可道,非常道”,门客为了避冯道的名讳,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苏东坡有个婢女,唤作春娘,才貌俱佳,东坡被贬黄州时,竟然以其换马,春娘责问东坡道:“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诗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言毕,春娘下阶触槐而死,东坡甚为怜惜,悔之晚矣。
在上古母系氏族社会,母亲受到尊敬和崇拜。而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受“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受“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礼仪的约束,能享有多少自由呢?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白居易的《卖炭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卖炭翁身上衣服单薄,寒风刺骨,却宁愿忍受严寒,希望天气更加寒冷一些,可见极度的贫困已经禁锢了人的心灵,禁锢了人的美好愿望。众生不得不负重而行。因为,生而为人,身系责任,来自家庭的、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责任,往往也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即便负重前行,那么能走多远?腾挪的空间多大?这取决于人的能力大小。
自由在哪里?习俗、时代、物质、制度、法律、道德、组织、责任、能力等,这些互相交织,进而搭建出一个框架,自由就在这个框架里。这个框架的空间越大,自由的空间就越大,自由就越具活力,越具创造力。突破了这个框架,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可能会坠落,也可能不复存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