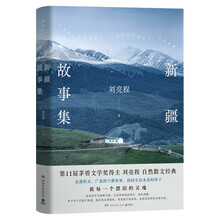公文包、报纸和糖
我小时候喜欢翻父亲的公文包。
父亲的黑色公文包是人造革的,狭长而扁,他时常挟在胳肢窝底下走来走去。里头装着的是一些油印的公文材料,还有一个装着卡片和几张钞票的真皮钱包。我曾把这些花花绿绿的卡片从钱包里抽出来,当作飞镖暗器扔得老远——嗖一下,就越过了院墙。或者是跑到小河边,用这些卡片打水漂。后来挨了一顿揍,才知道那是取钱用的银行卡和信用卡。
父亲翻查着公文包,悻悻地说:“唉,小把戏!还好!还好身份证找回来了。”
父亲每天梳着油光光的大背头,像模像样地把包挟在胳肢窝底下,就去忙工作了。那时,父亲刚进国际层压板公司工作,那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便不由得意气风发,天天都要精心地用啫喱水梳一个大背头。头发叫摩丝喷过,又浓密又坚硬,根根钢丝般分明,与港台明星邵昕很相像。父亲因为高中时文科成绩不错,又爱写文章,就被派去了公司的宣传科。
国际层压板公司在县城里,父亲跟着去了县城。不能常回来。
太阳从单薄的绿色纱帘照进来,屋子里的光线照出了莹莹的绿色,风吹动纱帘的时候,绿色的光线也随之波动,像是一汪布满绿藻的池水。我独处在这样透明清爽的客厅底下,便察觉时间过得缓慢而轻盈。父亲来来去去,也像是在顷刻之间。爷爷说,搬到县城,这是在赚钞票。但什么是钞票?就为了那些红红绿绿的印刷纸?我百思不解。我曾在祭祖时从燃起的火堆里抢救出一张,献给父亲,却遭受了他的斥骂,就更想不明白了。
父亲头年在公司宣传科工作时,不受人待见。因同去的,多是大学生。父亲只有高中文凭,自然为这批高阶知识分子所轻蔑。父亲也自有他的抵抗办法,就是回来后关上房门,把公文包卸下,狠狠地骂上一句:
“这批死读书的家伙什!”
没多久,父亲接过了编辑公司报纸的工作。这是一份重要的差事。
父亲回来后关上房门,把公文包卸下,笑哈哈地说:“这批死读书的家伙什!是时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父亲叼着香烟,开始编排报纸。但他厌恶学习新事物,凡事皆凭着一股蛮劲去做。既不了解编排的技术,又耻于问人,只能埋头苦工。父亲找来了长尺和铅笔,在纸上作徒手规划。他在纸上六分之一处作一笔直横线,模仿着隶书体写道:“国际层压板报”,右下角用小号字体写:“第一期”。反复细细勾勒几次,竟也写得像是印刷出的。
他每得一些进展,便在心中念叨着那些书呆子的名字。而后便是对稿件的编排。父亲找来了废旧报纸,对照着来稿,从旧报纸上剪下一个又一个铅字,用胶水粘于纸上,以尺做标,排列成文。第一期国际层压板报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剪贴字拼凑出来的。这活脱脱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术。
为争这一口气,父亲就在荧黄的台灯底下剪报。残缺的旧报纸堆在脚边,围成软软的一道新城墙。
新报纸编排好了。
他抽着烟,烟雾绕悬在他的头顶。他将这张用活字印刷术方法编就的报纸久久翻覆地看,满意地说:
“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的。”
我爱翻看父亲的公文包,这只人造革公文包的内容物,每回都不尽相同。我就曾翻到这张报纸,那是原版剪贴报的复印版。我将报纸从文件中抽出来,对着阳光细细地看,铅字就像是一只又一只爬动的蚂蚁。我在空中挥舞这张报纸,一边胡乱而张狂地啊啊大叫。我用这张报纸叠纸飞机,再哈一口气,纸飞机就可以飞得又高又远,飞到遥远的校场,直插靶心的十环。
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