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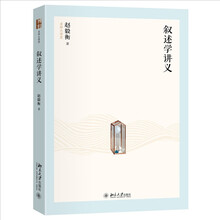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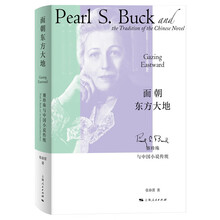





法国小说在20世纪经历了非常特殊的变化过程。在此之前,小说往往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按照因果律安排情节,并努力营造文学摹仿现实的错觉,这些原则构成了19世纪重要的欧洲小说基础。然而,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一些小说家——例如伍尔夫和乔伊斯——开始对这种小说创作传统提出挑战。在法国,这一挑战与20世纪几乎每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的创造都紧密相关。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通过探索摹仿小说的对立面,这些小说家也构建了一种真正的发展潮流。这一潮流具备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过程和发展进度,其中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是它的两个发展加速期。处于这一潮流中的作品尽管特点各异,但也表现出某个重要的共性,即它们都与以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为核心的传统摹仿小说拉开了距离,甚至发生了激烈对抗。亨利·戈达尔的《小说使用说明》即关注了这样一种革新性的批判潮流。本书共十四章,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通过种种形式创新来“反摹仿”的法国小说家及其代表作,清晰地呈现出二十世纪前七十五年中,法国小说所走过的一条反传统路径,并分析了这条路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通过这一分析,亨利·戈达尔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
《小说的危机和永恒》(节选)
通过虚构且只通过虚构,另一种想象回应着我们的想象所拥有的最私人的东西。现在有太多的小说被创作、被出版,以至于我们并非总能意识到这点,但一个开始写小说的人,他的行动是有胆量的。借助词语,他试图将你们内心深处告诉自己的关于情境、经历和地点的想法转化成故事,同时打赌这些词语也会将你们的想法告知给其他人。总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切都得以解决。除了人物、曲折的情节和描写之外,和我们有关的就是小说家了。他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创造这些人物、这些曲折的情节和这些他描写的地点上。如果我读到了小说的结尾,他就赢了。我们之间逐渐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后来转为一种默契,即当我们发现他的某个怪癖或举动时,我们并不会为此责备他。这种默契也促使我们思考,就像在阅读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小说时经常思考那样,当人物无缘无故地遭遇了许多困难时:他将如何让自己从困难中走出来,也就是如何从困难中脱身?虚构产生的乐趣和叙述特有的乐趣就在这段三角关系中汇合,在这段三角关系中,两个个体同属一个现实世界,他们通过各自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所投入的思考而进入到这段关系中。
上述协议还有最后一块“阵地”,即福楼拜在 1852 年的信件上所发表的将主题和风格对立起来的著名宣言,后来我们付出了许多努力来明确区分两者,而这些宣言可能也混淆了我们的感知。这种对立源于福楼拜对风格的根本设想,也许它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没有福楼拜为自己挑选的主题、人物和故事,他的风格会是什么?福楼拜每句话中标志性的冷漠和疏离是针对什么而言的?一部伟大的小说往往是一种贯穿全文的双重现实。讲述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词语在同一层关系上,无论何时我们都能将注意力从故事转移到词语上,反之亦然,更准确地来说,无论何时我们都更能将注意力调节至故事上,而非将注意力调节至词语上。逐渐地、甚至是同时地,我们从句子所描述的(人物、人物的言语、人物的行为,等等)和它描述这些的独特方式中体会到乐趣,而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独特方式,句子所描述的就等于零。
在我们打开的每一本新型小说中,我们都期待与小说家达成这种双重理解。在一些具体且分类明确的小说类型(侦探类、冒险类、间谍类或其他)中,没有风格,也没有个人写作。此外,这种写作只能被称为白色写作或公共写作,除非它表明是何种拒绝使其选择了这种白色,从而使其变得不再公共,而是具有了私人性质。在阅读中,我们也读过大量翻译过来的小说,这也是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然而,在我们用我们的语言读到的那些书中,有哪一本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在其伟大的场景中,是否真的留下了虽然沉闷却生动的口吻或回声?口吻或回声是读者与小说家达成默契的核心,随着我们深入地阅读,这种默契逐渐形成并最终出现,而那时,我们觉察到右手边还未翻页的纸张厚度在变薄,我们被迫意识到还剩下几页就读完了。于是,我们可能会后悔跳过了不重要的句子,尽管这是为了尽快看到小说的结局。所有的提示、所有的词语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来自我们长期以来快乐地跟随着的小说家笔下。每个词语都有可能延长这份始终可以神奇地存在的快乐,这份每次都相同却又有着新意的快乐,这份小说借助构成小说的词语而“持续”(tient)到底的快乐。在 20 世纪,我们能够找到体现虚构这种力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纪德对西默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说创造能力的迷恋。乍一看,这种钦佩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纪德凭借《帕吕德》和《伪币制造者》成为了最早怀疑虚构的作家之一,但是,在他的叙述中,他除了自己的经验之外,什么也没有写,相反,他必须衡量在西默农这样有效的虚构作品中,想象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在纪德向西默农表达敬意时,他承认,虚构和笑(人的本性)一样重要,尽管我们有时会认为虚构是过时的、令人生气的。
一旦我们喜欢上虚构带给我们的短暂体验,我们就很容易说服自己承认上述这点。虚构促使我们在虚构世界中生活一段时间,同时我们又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虚构也被打上连续性的烙印,无论何时,它总会和下一时刻连贯起来,但是虚构让我们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去经历这种连续性。从读第一个词开始,我们就知道虚构让我们参与到一种人生中,但我们对此毫无意识,这是一种逐步走向某个终点的人生。如同这种人生曾有一个开始那样,它也会有一个结局,一个它不停走向的结局。与这种人生有关的一切都是很重要的:各种行为、各种决定和各种曲折的情节。即便终点是死亡,但这个死亡也不同于等待着我们的那个自然死亡。
因此,最不起眼的虚构也会触及我们的本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盲目地活着,在等待、恐惧和短暂的任务中消耗人生,受困于暂停的时间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屈服于偶然性。我们最终失去了对某种目标明确的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不管怎样都一直存在,因为虚构会按照它所创造的生活的模式,令我们重新产生向往。一边是每一刻都不确定的逝去的时间,另一边是对这时间的整体意图和意义的确定,虚构通过在想象中实现这两者几乎不可能的联合,在我们身上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条件。通过虚构,小说潜在地承担起某种存在的价值。在《恶心》一书中,萨特借罗冈丹之口,表达了只想要在这个联合中看到诡计和欺骗的意愿,因为小说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的人物将走向的终点,决定了人物的前进路线,而读者将像对待自己的人生那样,在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去发现人物的前进路线。但是公正地看,这个提醒半真半假。是读者,而非小说家,单纯地去阅读小说,对读者来说,这段阅读就是去经历两段自相矛盾的时间,而这种经历会让读者去探索他存在的根本。
虚构也并非我们探索自己存在的根本的唯一方式。无论以哪种方式,小说总是和时间相连。探索另一种时间性使相当一部分小说以对抗虚构为创作方向。而虚构又和时间的连续性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连续性会反过来对抗虚构本身。但是连续性只是我们经历时间的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还要将“现在”作为对抗目标,连续性使“现在”消失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但对我们来说,“现在”比连续性有更多的瞬间现实。我们知道“现在”很短暂,但我们无能为力,“此时此刻”(sur le moment)我们只能生活在“现在”,“现在”是唯一的、不可超越的、自给自足的—我们生存的绝对意义。当小说改变连续性,试图通过词语抓住这个“现在”时,小说就向自己提出另一个挑战,这个挑战证明要求读者付出努力是合理的。20 世纪以这个新目标为方向而创作的某些小说和某些文本,也被我们视为人类这个尝试的成果,而这个尝试一直存在、一直有待重新开始,并希望通过某种艺术的方法让时间站在这些创作者这边。
西蒙在其创作后期写了两本书,它们都取材自他的经历且都是小说:第一本是《刺槐树》,它极其自然、毫无挑衅地讲述了一个有序展开的故事;第二本是《植物园》,像他之前的作品那样,故事不连续、无序,甚至还有形式上的新探索。21 世纪初的小说读者们,像这样两种形式不同的小说创作也将是我们未来的创作。今后,我们既会费力地去阅读一本叙事不连贯的小说的前几页,也会平和地去阅读一本叙事过于连贯的小说的前几页——然而,前提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使用虚构的新方式,一种能在语言中遵循另一种不同于自愿和有意识的意义线索的能力。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无论书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都能从中找到工作和日子总让我们失去的一些感受:人生的复杂,我们对价值的需要,我们在寻找价值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不确定性,还有最根本的,对我们存在于世的震惊。
让小说家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