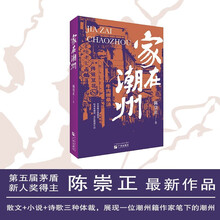《现代转型体验: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
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本体性安全,是更为重要的安全形式。本体性安全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相连,所以,人们在心理上经常希望能预料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和周而复始的东西。“如果这种惯常性的东西没有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或改变。”①可见,确定性是个体获取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人类的梦想和持续追求的对象。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本体性安全是自我心理组织系统的基础,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恒常所具有的信心,其功能在于控制或排解焦虑,使个体获得安全和可靠的感觉。本体性安全的获得还取决于自我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新时期以来,乡村被现代化洪流代人深刻与复杂的转型中,当代文学多有表征:传统与现代、美好与糟粕、共时与历时都在文本中具现,这些嬗变既有乡村伦理的剧变,世外桃源的污染,也有价值观念的裂解;既有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有担心发展落后的心理紧张,还有乡村最大群体——留守妇女、儿童的不安全感等,大大改变从前的“确定性”“连续性”“可靠性”,从而成为乡村与农民不自觉、却是更为根本的内在体验。李云雷指出,“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当代的‘离乡者’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得太快了,而且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以及转基因食品、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等问题,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故乡’已经消失了,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而这一变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似乎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表现。”②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乡村大量青壮年男性的外出打工,遗留在乡的弱势的留守妇女和儿童的安全便成了乡土最重要的心理焦虑和社会事件,成为广袤乡村的普遍性问题、最大公约数。在众多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乡村异化权力的滥用、乡村中老年男性的觊觎、窥探、欺辱乃至性骚扰,对留守妇女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一人独处的寂寞无助、对丈夫在外的担忧,都会转化为内心的强烈焦虑、不安全感。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①吴治平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涂春奎的小说《锦江湾》、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等文本叙述了这样的“安全焦虑”故事。在小说《一个人的村庄》以“我”的经历,书写了乡村留守妇女不安全感、焦虑、无助和愤怒。独自留守乡村的“我”成为被村里众多男人觊觎、性骚扰的对象,不管白天黑夜,不断有男人像幽灵和饿狼一样游荡在“我”家后院,他们有的死皮赖脸地用话语调戏,有的隔窗公然窥视,有的动手动脚揩油,有的半夜敲门、翻墙,有的甚至直接强行躺在“我”的床上。这一切令我无助、恐惧和焦虑,不安全感使我时时处于高度紧张、戒备、自卫的状态,“我”痛苦无助、疲惫不堪却只能默默忍受,勉力支撑,最后,“我”终于爆发了,用菜刀将床上的人砍死,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解脱和久违的快乐。可以说,处于法律缺位的乡村,性骚扰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所带来的家庭、社会、心理问题层出不穷。“我”的“施暴”也反映了她们真实的心理困境、沉重不堪的心理焦虑。
此外,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日益成为农民本体性安全的新焦虑和现代新体验之一。由于农民大量离乡离土进城,他们作为城市外来阶层,城市的无法融入、乡村返而不得的“悬置”状态,常常会让他们感受到精神文化的错乱和苦闷焦虑。读者在尤凤伟的《泥鳅》、贾平凹的《高兴》、张继的《到城里受苦吧》等新世纪乡土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城乡“零余者”、文化“边缘人”,他们在城乡交叉地带颠沛流离、张皇四顾,呈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长久而痛苦的身份焦虑。自我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是身份焦虑的根源。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认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①德波顿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探索身份焦虑的根源,他告诉我们,身份焦虑的本质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担忧我们失去身份与地位而被夺去尊严与尊重。身份焦虑在中国各阶层普遍存在,但在离开赖以生存的村庄去城市或者其他地方打工的农民工身上尤为明显。说到底,身份焦虑实质上是生存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农民与曾经熟悉又巨变的乡村及打工的城市发生着错位,“农民”身份让他们尴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尊严,甚至更多的是偏见与歧视。他们实实在在发生身份转换、认同涣散——当代“新农民”谱系的裂解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迷失与错乱随处可见。此间,乡村呈内在分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愚昧/文明、富裕/贫困、宗法伦理秩序/道德失范失序、乡规民约/法律法规、邻里情谊/人际疏离、田园风光/污染圈地、跨越发展/节奏缓慢、笃守平静/心理失衡等。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无论是精神形态,还是感觉结构,都远离古典时代,当代农民被“现代化”转型塑造成“新农民”或“历史中间物”。“农转非”过程中,裂解为“新农商”“新农工”等多面向角色。这是农民在应对现代化出现的由表及里、新旧杂糅的身份混乱与文化冲突。其所新者不全新,有农民艰难获得的现代性因素,也有畸形发展所形塑的变异;其所旧者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又与国民劣根性纠结,撕扯得鲜血淋漓,显露文化根性相同的一面。新旧杂糅,传统与现代锯齿般啮合,带来现代性转型期间的分殊与焦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