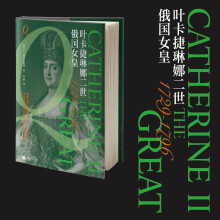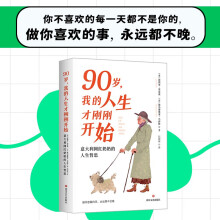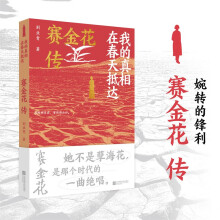《我飞虎队女兵》:
一、学生时代
1.我的父母兄姐
我的家乡昆明,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1921年11月12日,我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当时,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都特别喜欢我。母亲曾经笑嘻嘻地告诉我一个小秘密,我出生时,父亲为了我起名字之事整整琢磨了半个月,最后决定起名“张凤岐”。母亲说,“凤岐”二字来源于一个典故,发生在周朝将兴盛前的陕西省岐山县。典故是这样的:岐山有凤凰栖息呜叫,人们认为凤凰是由于文王的德政才来的,这是周朝兴盛的吉兆。所以,也以凤比喻周文王。陕西省岐山县是周朝的发源地,也叫西岐。当时《竹书纪年》中还记载:“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鷟鸑呜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我听了直点头。从母亲那里我还知道,外公陈肖普是个读书人,《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背得滚瓜烂熟。不仅如此,外公还是云南著名的书法家,有很高的书法造诣,到了89岁高龄还挥毫不辍。父亲张兰也很有才华,曾参加过清末科举考试,在云南省城,一举中了秀才。辛亥革命后,父亲在云南省法院谋得一个小职务,为了全家生计,每天起早摸黑地忙碌,46岁那年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当时,医疗条件很差,肺结核几乎是绝症,连医生都直摇头。病情日复一日严重的父亲,只得拖着病躯继续操劳。即使再辛苦,他也不会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记得有一次,他分别把孩子们叫到床边谈话。我见到哥哥姐姐从父亲房间走出时,神情都十分严肃。当把我叫到跟前时,父亲拉着我的手说道:“我们张家不管男孩、女孩,重在读书成才。你要像哥哥姐姐那样用心念书,学有长进。他们放学回家先做功课再玩耍,有时家里停电,也能在煤油灯下做功课。你现在还不懂事,等长大以后就会知道读书的重要。‘读书改变自我’,这句话有很深刻的道理。我希望你从小好好读书,打好基础,为全家争气。”父亲讲的这番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不久,父亲去世了。一遍又一遍以泪洗面的母亲撑起了这个家的一片天。所幸,我的哥哥姐姐都学有所成。大哥张士敬学习成绩非常好,他不仅数学很出色,英文也很流利,从云南省师范学校男生部毕业后先进入昆华女中教书,后进入云南省财政厅工作。由于业务能力强,很快就被提升为部门主任,他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经济收入承担起家里日常的开销。母亲不仅把家里的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让所有孩子都上学。在她的教导下,二哥张士厚不但好学上进,而且富有正义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爱国进步组织。
除了两个哥哥外,我还有五个姐姐:大姐张凤书,二姐张凤鸣,三姐张凤梧,四姐张凤琴,五姐张凤翔。我们姐妹六人,互爱互助,和睦相处。令人扼腕的是,三个姐姐都命运多舛:大姐张凤书在书法绘画方面很有特长,可惜的是,她从学校毕业不到两年就染上肺结核而去世了;二姐张凤鸣曾做过代课老师,后来也染上了肺结核,很快撒手人寰;四姐张凤琴毕业于昆华女中高中部,抗战时期身患重病,因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医院和药房遭到破坏,无法救治而去世。所以,只留下三姐张凤梧、五姐张凤翔和我。
2.感染爱国热情
兄弟姐妹中,数我最小,所以哥哥姐姐都很关心、照顾我,他们孝敬父母、发奋读书、关心他人、正直为人的一言一行自然也影响着我,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在我的学生时代,对我的成长有过重要影响的,是我二姐、二哥、表妹,以及二哥的同学聂耳。
二姐对我的影响,除平时学习、生活上的关心外,还在于她的进步思想对我的感染。那是二姐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学校推荐为代课老师后。那时,她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还独自做教具,经常让我帮她搭搭手,所以,那段时间我与二姐很亲近。当时,日本已经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黑云笼罩着华北,“祖国大好河山岂能被日寇铁蹄践踏”,“我们不能做亡国奴”,是二姐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学校里,二姐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反抗日本侵略外,还和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抗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当时,街上天天有时事快报卖,报上有很多关于目本侵略军入侵情况的报道,二姐经常买快报给家里人看。那时,我已是十余岁的学生,从快报上看到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中国老百姓的报道,激起了我对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的无比痛恨和满腔怒火。此后,二姐还绘声绘色地和我们讲述她上课时给学生读快报,有的学生当场失声恸哭的情景。二姐的爱国激情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时,对我的进步有影响的,还有表妹张玉岚。她比我小几岁,我们是昆华女中的校友。她在昆华女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游行,还是爱国学生组织的重要成员。她从昆华女中高中部毕业后,毅然离开了昆明,奔赴陕西延安,投入抗战热潮。记得,我们在昆华女中读书期间,表妹总是让我一起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无论是制作标语旗帜,还是上街游行,我在表妹的鼓励下,也热情高涨。她奔赴延安后,我们失去了联系。1996年,我退休后回到昆明探亲时,三姐告诉我,表妹离开昆明去延安投身革命后,辗转各地。解放后一直留在北京工作,现在已经离休。得到这一信息后,1999年我特地到北京与她见面。一起回忆在昆明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她告诉我,她在延安入了党,在革命队伍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全国解放后,她在北京建立了家庭,组织上先后安排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队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部级干部。其间,她曾经回过昆明几次,游历故乡的山水旧地,探望故里的父老乡亲。
除二姐与表妹对我的影响外,二哥与他的同学聂耳,是我学生时期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得那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天,二哥带回来一个男同学,他,高高的个子,英俊的脸庞,整齐的头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对我母亲非常有礼貌。每次来我家,总是彬彬有礼地向我母亲问好。自然,母亲也十分喜欢这位小客人,不是让我们倒茶,就是留他吃便饭。随着来我家次数的增多,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亲切地叫他“聂耳哥”,他真挚地称我“小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