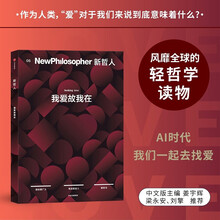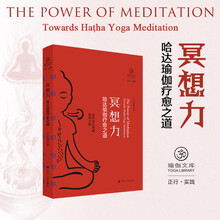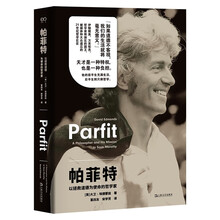这是一种何等深奥而又隐蔽的过程!谁要是说某个孩子说出了“第一个”词,那将是何等地愚蠢。谁要是试图让孩子在一种同人类语言完全隔绝的环境中长大,而后从这些孩子第一次牙牙学语的发音方式中去发现一种真实的人类语言,以此来揭示人类语言的起源,并把这种试验冠以“原始”语言的创造,那将是何等地荒唐。这类想法的荒唐性在于他们希图通过某种人工方法排除掉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包围着我们的语言世界。实际上,我们总是早已处于语言之中,正如我们早已居于世界之中。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人学习说话的过程作了最机智的描述。亚里士多德的描述所指的不是学习说话,而是思维,也就是获得一般概念。那末在现象的变动中,在不断变化着的印象之流中,似乎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如何产生的?显然,这首先是由于人有保持的能力,也就是说记忆力,记忆力使我们能够认出哪些东西是相同的,而这是抽象的最大成果。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中处处可以观察到一种一般现象,这样,从我们称之为经验的认识的积累中,就渐渐地出现了经验的统一。一般知识在这种方法中表现为一种处理经验到的材料的能力。于是亚里士多德问道:这种一般知识究竟怎么可能产生?显然不是通过以下这种方法:即我们体验着一个又一个的现象,而后,突然间,当某个特殊现象再一次出现并被我们确认为与以前体验到的现象一样时,我们就获得了一般知识。这个特殊现象本身并不能通过某种表示一般的神秘力量而与所有其他特殊现象相区别。毋宁说,它与其他特殊现象一样。但是实际情况是,关于一般的知识确实是在某个阶段产生的。是在哪个阶段开始的呢?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一个绝好的比喻:一支正在溃逃的部队是如何停住的呢?显然不是由于第一个士兵停住了或是第二个、第三个士兵停住了。也不能说相当数目正在逃跑的士兵站住时这支队伍就停住了,显然也不能说部队是在最后一个士兵收住脚步时停住的。因为部队并不是在最后一个士兵停住时才开始停止前进。从开始停止到完全停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支部队是怎样开始停步,这种停步的行动怎样扩展,最后直到整个部队完全停步(也就是这支部队再一次地遵守统一命令),这一切都未曾被人清楚地描述,或有计划地掌握,或精确地了解过。然而,这个过程却无可怀疑地发生着。关于一般知识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因为一般知识就是这样进入语言的。
我们所有的思维和认识总是由于我们对世界的语言解释而早已带有偏见。进入这种语言的解释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中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语言是人的有限性的真实标志。语言总是超越我们。个体的意识并不是衡量语言存在的标准。实际上,在个体意识中并不存在口头语言。那末语言是如何存在的呢?显然不可能离开个体意识而存在,但语言也不仅仅是许多对自身来说是特殊意识的那些个体意识的集合。
没有一个人在讲话时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讲话。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对他正在说的语言产生意识。例如,当一个人开始说什么事情时产生了犹豫,因为他发现自己将要说的事情显然有点奇怪或滑稽,这时他才会对自己讲话所用的语言产生意识。他想知道:“真的可以这样讲吗?”在这种时刻我们会意识到我们讲的语言,因为这时语言没有像它固有的情形那样工作。那末什么是语言所固有的情形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