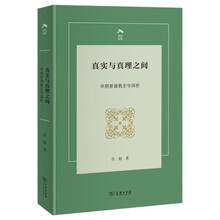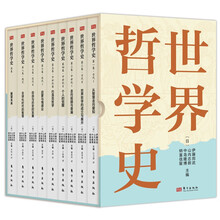夏威夷,午夜已过,偶尔有远处传来的飞机起飞或汽车驶过的声音,相伴的也有凉爽的风吹动窗的声音;否则,人们正在酣睡,十分静寂。
我的英文著作《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马上要出中文版了,需要写个《序》,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课题,它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让自己的思路回到这个问题上,油然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时间过得好快。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已花去了我十几年的时间;起初决定做这个研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不过对当时的回忆,立刻激活了心中曾经的兴奋,也带来现在的欣慰。
记得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美国求学的一些年,我经常发现,在中国学到的西方学术概念所带有的含义与它们的英语对应词汇原本的含义相去甚远。比如,汉语“超越”不含英语“transcendence”的本质割裂性的深层含义;“辩证法”较之“dialectics”,更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矛盾”与其说是英语“contradiction”,不如说是“一矛又一盾”;“普遍性”不是“universality”,而是“无处不在”;英语“unity”通过汉译变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统一”,也基本失去了它原有的深层含义;“理论”一词,延续着的本是宋明理学的含义,已不含英语“theory”“未经证明假设”的基本含义;“实践”和“practice”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样互不相识。
于是,我开始想,中国人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否不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几乎是在思索这一问题的同时,我接触了郝大维、安乐哲两位比较哲学家关于中西方思想传统存在结构性差异的论述。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上有一种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那就是两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乃至两种语言上的结构差别。这是在语言具体使用情势和场合中双方无法察觉的东西。明确地说,即一方面是西方人心灵深处的超绝主宰体的宇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结构,另一方面是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变式互系性思维结构。不过,作为一个短《序》,这里不能展开阐述这两个迥异的结构。我只是点出,如我在上面提出的,通常被认为是可以互译的汉语与英语的对应词汇或概念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结构差异。这是问题的关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