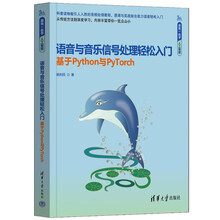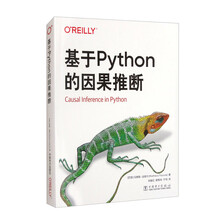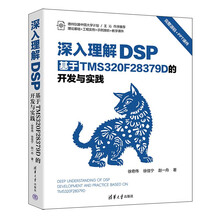上篇 种子的智慧
一切都和种子有关。
我们几乎是在谷物大规模牺牲的早上开始我们的一天的:我们用脱粒谷子的种子熬成稀饭,用大豆研磨成豆浆,把大麦的种子做成各种形状的面包,用橄榄的种子制成透明的油汁,我们把辣椒切碎了撒进面条汤料中……在我们的厨房里,还有无数植物的种子在这个早晨开始之前就已经死在各种包装袋中,并被染上各种颜色,只为给我们的味蕾增加一些滋味。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是,这个似乎是征服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被植物巧妙利用的过程。我们用日常生活参与进植物的各种诡计之中,我们食用它们,同时也在有条件地帮助它们保存和传播种子。这个表面上利己主义的行为,背后是地球上广泛存在着的一种利他模式:与人类一样,其他动物和微生物们也在衣食起居中暗地里助植物一力。因为植物种子和动物一样,有时候显得无能、弱小、恐惧,但又慷慨、勇敢和有诗意,并且和人类一样热爱旅行和远方。
种子的出现最初是想要调和与死亡的关系。自从地球上有了物种之后,死亡就与之如影相随。在死亡与新生之间,种子是一个有效的过渡。对于地球上很多物种来说,死并非一个单纯的消亡过程,而只是一次大动干戈的修补活动。因为我们的基因里存在着很多令人遗憾的缺陷,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有着无法预测的变化,对付这一切,我们唯有谦逊地改变自己,通过死亡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植物种子正是担当这样一次次修补大任的使者。在这方面,种子还是节约的典范,因为有死亡,它小小的身子里必须包含各种关于祖先的信息,以便在成长时模拟它的父辈,同时也为地球节省一些花样。种子的形状不像它的父母,为了安全,它必须浓缩、浓缩、再浓缩并伪装成一种假死状态:安静、紧凑、木讷、笨拙——但只要有机会就准备移动和发芽。
延绵,基本的自我,真正的时间,生命冲动,这些都是种子所具有的特质,哲学家伯格森说,这也正是构成世界本质和基础的几个重要因素。生命太过复杂,宇宙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一刻不停地给我们创造出新的物种来,但宇宙又需要保持基本的面貌,于是就发明了种子。就此而言,每一粒种子可以说都是宇宙中一个生气勃勃的仓库,每一粒种子也都是一份记忆,记录着它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时间、光线、色彩,宇宙所拥有的秩序,自身的智力变化,以及在它小小的身体里能够讲述的其他东西。但种子也有自己的寿命,寿命短的种子只有几小时、几天,长的却有几个月、几年、几十年甚至几千年。20世纪50年代,有人曾在中国辽宁省普兰店泡子屯村的泥炭层里发现了一些1000多年前的莲子,当科学家们用锉刀把古莲子外面的硬壳锉破后,浸泡在水里,这些莲荷的种子竟抽出嫩绿的幼芽来。
种子起源于3.6亿年前,作为一个保存信息的装置,它是植物们最为复杂的器官之一,也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特有的器官。从它的生理结构上讲,种子是一个经由胚珠通过传粉、受精形成的用以延续植物生命的载体,同时也是植物向外传播和扩散的载体。目前世界上有26万多种种子植物,中国有3万多种。可以说,正是种子的出现,使得种子植物成功地取代了蕨类植物,让一部分植物长得更高大,一部分植物能够开出更美的花朵,也让一部分植物能够成功地在地球上作各种远途旅行,地球的面貌也由此变得更加缤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3.6亿年来,正是种子们依靠着一种有技巧的接力赛,将植物的智慧和勇气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依靠风,依靠雨,依靠水,依靠动物邻居,依靠自身的机关设置,在瞬息万变的气候中,把美丽、生机、丰饶和未来带给了地球。
加拿大作家曼古埃尔说,我们的存在像一条双向流动的河,从数不清的人名、地点、生物、星球、书籍、仪式、记忆、理解和石头(我们总称为世界)等等流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盯着我们的面孔;再从那张面孔,那个围着某个隐蔽中心的身体,从我们称为“我”的地方流向每一个“它”,流向外界,流向远方。对于种子来说,它们的存在也是一条双向的河流:从数不清的年、月、日、分钟、秒,流向它的内部,围绕着自己内部那个隐匿而黑暗的中心,再流向大陆、岛屿、山川、河谷,流向远方。
种子是一个关于未来和过去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内部和远方的故事。
在生存问题上,动物和植物都倾已所有,向大自然奉献了它们所具有的智慧、真诚、勇敢和狡诈。或者说,面对大自然,我们的行为其实并无善恶和褒贬,所谓“恶”,不过是由缺陷造成的。正是因为有缺陷,才使得某一事物和某一物种诱惑另一事物和另一物种,使得另一事物和另一物种压迫某一事物和某一物种。对于植物的种子们来说,体型过小或体型过大(例如天麻和巨籽粽),长得其貌不扬,没有良好的旅行装备,童年过于压抑(例如生活在丛林中),父母长得太高或者太矮(俗称不能“拼爸”也不能“拼妈”)……这些都是阻碍似锦前程的“缺陷”,而相应地,克服这些先天的贫乏,抛弃父辈的疲倦,懂得梦想,懂得借力,懂得利用,懂得“欺骗”,把地球上一切存在都视作可借用的条件,便是它们的智慧。
可以说,正是贫乏和缺陷,将种子机智的界线衬托得更加分明!
扰邻的“射手座”
生存技能:自制发射武器
生存等级:五星
并不是所有关于种子自力更生的故事听上去都很辛苦。对于有些植物来说,自力更生不乏自娱自乐的成分,比如喷瓜(Ecballium elaterium)。
对于选择喷瓜做邻居的其他植物来说,与它为邻就意味着必须克服对于这位老兄危险又无厘头的恶作剧的惊奇。喷瓜生活在地中海沿岸和西亚一带,是一种葫芦科植物。它外表朴素,行事低调,无意出风头,就是开花也是只开一种接近于叶片颜色的黄绿色。但别高兴得太早了,一旦这位老兄有了“情况”,它周边就不得安宁了。喷瓜成熟时,果柄和果实结合处会脱落,此时具有压力的浆液就像揭开盖子的可乐一样,从果柄着生处的小孔喷涌而出,裹挟在其中的种子就此被一并喷了出来,距离可达数米之远。幸运的是,这位射手枪头并不准,也并非想瞄准什么,只是心怀一个朴素的愿望,那就是让它的种子能够够得着土壤。在播种这件事上,喷瓜的手段虽然有点大大咧咧,且有扰邻之嫌,但它却是一位善于选择细节的动力学家。为了把它的种子送出家门,它那套物理装置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心设计过,比如种子的质量、体积、压力以及最佳射程。不过选择自带一套喷射装置的植物并不止喷瓜一家,凤仙花、酢浆果、羊蹄甲、洋紫荆也会在宝宝出生时就为它们备好这样一个育婴装备。洋紫荆果实成熟时,一有风吹草动,果皮就会裂开,借着果皮反卷的弹力,远远地将种子弹射出去。有些蒴果及角果果实成熟开裂之时也会发射它的种子,而且速度非常快,让人措不及防,例如乌心石。这些植物都指望在繁育后代这件事上能够自力更生,最好不要求助于他人。
不过,出其不意地把种子喷射出去,总是一种带有一厢情愿的暴力之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邻居都能领会和理解它们的远大意图——何况有些邻居们并不真的认为数米之外就是远游,设计这么复杂的一个装置,只为去三四米之外的距离!与它们相比,依靠地球引力来传播种子要显得礼貌、优雅和矜持得多了,也比较受它的邻居们欢迎,只要不生活在它的树荫下,比如毛柿及大叶山榄——它们只在自己的地盘上瞎胡闹。椰子树也是一个极其自律的角色,不过它只是别无选择,因为果实又大又重,树又长得高,无法像喷瓜那样把种子弹射出去,要把这样的大家伙发射出去,得在它的枝头架设一座大炮。面对这个问题,它的亲戚巨籽粽可能更加头疼。巨籽粽的种子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种子,有记录的巨籽粽种子最重可达17.6公斤,难以想象要怎样的发射后台才能将它们送出去!像动物一样,植物们在设计自身时并不想浪费一些无谓的材料(有些吝啬的动物为了节省甚至都采用了雌雄同体的方式)。如果没有像喷瓜这样一种小巧又精确的装置,有个最为保险的办法就是凭靠地球重力——总有一天,地球的重力会捎走它们的孩子,让它们落入土壤的怀抱,之后在风雨数度的洗礼中,让它们完成传播基因的使命。
于是,让种子自由落地是很多植物会选择的策略,当然有些是出于自愿,有些只是出于无奈,但选择自由落地意味着种子们可能会失去一个锦绣前程。几乎所有的植物都知道,让种子留在自己身边,意味着让它参与与自己的生存竞争,空气、土壤、阳光及动物的粪肥,这些都是有限的资源,它们不愿意让更多同类来分享,竞争不言而喻地会伤害母子感情。在这种时候,我要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把陈词滥调颠倒过来,看到爱所造成的损害——如果我们把种子留在自己身边称作爱或者美德的话。很多植物就这样作出了让自己的孩子去远方的选择。要让每一粒种子除了有一个故乡,还应该要有一个异乡!无须替它们担心,植物们早就给它们的种子准备了这样一个旅行包,比如椰子树。椰子树希望它的后代能够觅到他乡,去远方打拼。它长在海边,为的就是可以让种子们日后有一个去航行的港口,同时,几乎所有的椰子外壳都又硬又牢固,就像一只小舟,适合远洋。从树上落下来后,椰子们无须担心短时间会弹尽粮绝,因为壳里面食物丰富,可供它漂流个十天半月的,它们的外壳也能保护它们不被海水侵蚀。当某个浪头把它们冲上某个海岛后,它们马上就可以在岸边的沙地上找到新的归宿,不久后会长出一片新的椰子林来。
睡莲也是一个很为后代操心的家伙。它们终生生活在水中,但并不希望“儿女绕膝”,也就是说,睡莲也希望自己的后代可以离开自己去开辟新的疆域。它们给它们的种子准备的旅行礼物是一些海绵状的外壳。当它们的果实成熟后,这件海绵外衣能够让种子们浮在水面上,这样,旅行起来就会很方便,也无须用力。随着水波,睡莲的种子就能愈行愈远,直至找到自己称心的栖居地。
乘风去旅行
生存技能:利用风能
生存等级:三星
我们极力想抑制的每一个冲动都会使我们郁郁沉思,令我们不快乐。旅行对于植物来说就是这样的冲动。如果种子不旅行,植物就没有希望。
最简便的旅行方式就是乘风而去。
但搭乘风作为驾座对种子们的体型和体重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没有天生的轻灵造型,就如椰子树或者睡莲,那是无法在空中飘浮的。热衷于以风作为交通工具的种子都是有备而来的,不是自带飞行器,就是体型微小如同尘埃,比如天麻。天麻的种子非常小,就像灰尘一样,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楚。天麻的种子皮薄而透明,其囊状的结构可以将黄色的椭形小胚包裹其中。为了便于在风中飞行,天麻通过在种皮表面形成众多的蜂巢状纹饰来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这样的细节设计极易随风和气流进行长距离飞行。不过说到小,天麻并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烟草的种子也很小,5万粒烟草的种子只有7克重(5万粒芝麻种子有200克重)。5万粒四季海棠的种子只有0.25克(是芝麻的千分之一)。斑叶兰的种子最小,5万粒才有0.025克,1亿粒斑叶兰种子才50克重。斑叶兰的种子除了随风飘荡,已经别无选择了。这么小,这么轻,它几乎没有行李,可以随随便便去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只有一层薄薄的皮和一点点借自己发育所需的养料。为了旅行,它作出的牺牲也是很可观的,在飞行途中,因为脆弱和供给不足极容易夭折。
乘风旅行的植物除了特殊的结构,比如轻灵的身体之外,其实植物本身是否高大也很重要,因为种子离地的距离越高,落地的时间也就越长,所散布的距离也就越远。也就是说,当种子选择飞行来旅行时,从哪里起飞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对于杨柳科(Salicaceae)植物的种子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树的高度足以让种子做一趟远途飞行,借助树高的优势,这些带绒毛的种子可以飞到数公里之外。当然,前提是杨树和柳树这些大家伙长在空阔之地,如果是在茂密的森林中, 空气流动较差,种子们就不会这么好运了。就是风再大,种子们也没法飞得更远。但这个难题也被一些聪慧者克服了。有些植物为对付这种情况专门为种子准备了一件精良的飞行工具:一对翅膀或者一些毛毛。特别是一些菊科植物,它们喜欢用降落伞来飘飞,当花季过后,花瓣会收拢起来,然后结籽,之后张开它们新的“花形”,吐出带着降落伞的种子,比如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和昭和草[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Benth.) S. Moore]。蒲公英的果子上长了很多冠毛,一旦果子成熟,这些冠毛就会撑开,就像一把降落伞。蒲公英的一生只有在种子们飞扬起来才算到达它生命的高潮。此时,它会往前飘啊飘,擦过紫羊茅(Graminae)的叶尖,越过一只蜜蜂毛茸茸的脊背,躲过一颗刚刚从山毛榉上(Fagus sylvatica)滑下来的露珠——它把眼前所见的一切都视作远方,尽管实际上它的种子只能落在几米远的地方。的确,对于一棵几乎一生都在一个地址上的植物来说,真正的重要性是在它自己的目光中,并非在所看到的事物上,只要有一对可以远视风景的眼睛,就是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整个宇宙。心灵上的远方比地理上的远方更为重要!
紫葳科木蝴蝶(Oroxylumindicum)的种子也具有薄如蝉翼的一对宽翅,可以支撑种子借着微弱的上升气流在空中滑翔,或在一阵大风中翻飞至远处。猫尾木(Dolichandrone cauda-felina)的种子也用滑翔板旅行,它的滑翔板造型就像一条猫尾巴:它们的种子长近半米,呈淡灰色,外面披挂了一层绒绒的毛。这条“猫尾巴”很管用,当它们悉知雨季要来临,就会在某天刮风的时候,让“猫尾巴”裂开,飘出带着翅膀的种子。给自己的种子一个有保障的人生,这是所有植物都孜孜以求的,可是大自然有时候会与它们针锋相对,自带飞行器的前提是一定要选择在晴天、有风的日子里出发,一旦某段时间暴雨不断,就不要再做旅行的美梦了,当然有些专门靠雨来远游的种子除外。
我们倾向于认为热爱旅行的种子们所要逃离的不是一个环境,还有可能是其他让它们感到不适的东西:陈旧的生活,狭隘、目光短浅的心态,隐私的缺乏,差异的抹杀,等等。在所有赞美风的人类诗歌中,风和追逐风的人都会被赋予这样一种性情和品质:自由不羁,热爱不确定性,热爱无常,爱慕远方,同时还要有旺盛的精力和永远的好奇心。我们被抛入存在,就像一粒子弹从枪管中射出那样,弹道已经被绝对地限定了,但在飞行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绝对的弹道上跳个舞。作家木心说,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或者说两样东西绝对地控制着我们,一是规律,二是命运。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难逃它们的独裁。风可能是一种试图用命运来克服规律的事物。规律是乐观主义,命运是悲观主义,事物的细节是规律性的,而事物的整体却是命运性的——在细节上大自然从不徒劳,但从整体来说,大自然整个儿徒劳。
比如,一颗种子费尽心思离开它的父母去了一个理想的伊甸园,可它最终逃离不了死亡的结局,它被其他的种子代替,其他的种子又被更多的种子代替……
地球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种子被代替又重生的循环往复的故事。
搭乘动物公交车
生存技能:动物公交
生存等级:四星
几乎所有的植物都知道,与动物们搞好关系是有必要的。
将动物们视作一种权贵或者吃得开的邻居,关键时候攀龙附凤总会给它们的生活带来某种实惠,比如,动物们甚至可以成为它们的坐骑。
哲学家加塞特说,对于一个不朽的生命来说,汽车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但对于那些生命时间有限、终有一死的动植物来说,征服距离与停滞却是非常有必要的。
动物有时候就是植物们用于征服距离与停滞的汽车。
苍耳(Xanthium sibiricum)就经常搭乘这样的汽车。冬天很快就要来临,在第一场寒流到来之前,苍耳们已经在江岸做好了旅行的准备。几天前,一场细雨斜斜地划过臃肿江面的水流,江水下面,沙子将那些圆溜溜的石头牢牢地抓在自己身边,好让那些贝类和小虾有安居之地。这几天也是鲟鱼们产卵的季节,几乎每天,鲟鱼们都在等着水温下降,好使它们的宝宝有个舒适的产房。每年都要光临的冬季并非意味着枯竭,而是孕育,但秋季一定是个忙碌的季节。岸上,小体型的动物们正在忙着收获和储藏食物,它们经常摩肩接踵地从苍耳身旁经过,从而留下一堆难闻的气味。苍耳们几乎每天都在打量它们的邻居,以便寻觅到合适的机会,将身体凑上去,然后把刺毛上带有倒钩的种子粘到它们身上。经常出现在这一带的是野兔一家,今年它们家产了五个小宝宝,因而父母们显得非常辛苦。有时候田鼠也会很快地从苍耳身下窜过,离苍耳最近的这只田鼠是个单身汉,它几乎每天都要来洞穴外面观望一番,却什么也不做。对苍耳种子来说,这些动物都是不错的交通工具,尽管它们对于目的地在哪儿这件事显得有点困惑。自从一年前跟着一个顽皮的小孩来到这里之后,苍耳们还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它们也不知道一年的时间有多长,因为它们从土壤里出来时外面已是春天,也就是说,眼下是它们的第一个秋季,它们对即将来临的冬季也一无所知,但看到很多植物开始抖落树叶,很多动物又变得异常勤劳,多少对此心怀一丝惊恐和困惑。身上的果实变得越来越坚硬,果实上的那些小倒刺也变得越来越锋利,是时候让它们离开自己了!苍耳们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衰老,对于冷空气也越来越不能适应,风中到处都是腐叶和尘土的气息,现在,它们还有最后一点力气,它们将最后残余的力气用于观察每天都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动物邻居。它们知道搭乘它们的方式:那就是动物们能带它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几天前,甚至有几个男生采下它们的几粒果实偷偷扔到了走在他们前面的几位女生的头发和裙子上。苍耳不知道这些随人类远去的种子最后会有怎样的栖居地。但它们知道,这是它们祖先一直以来沿袭的方式。
车前草(Plantago depressa Willd)也在等着这样的机会。车前草长得矮,几乎紧贴地面,这使得车前草无法获得像苍耳种子那样多的出行机会,不过它自有其他的交通方式,例如麻雀、乌鸫、螳螂、纺织娘,这些经常光顾这片草地的小动物很容易就捎走它们的果实。车前草的种子不像苍耳大摇大摆地就搭上动物们的顺风车,因为体型小,车前草的种子几乎都是悄悄地粘在动物身体上的,而且动物们多数情况下也不知情。实际上那些想以动物作为交通工具的植物种子都是私底下会使点手腕的,无能无德很容易会错过机会,比如苍耳种子上的倒刺,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种子上的暗器。蒺藜果实两侧有两对尖锐无比的刺,硬如铁钉,能够刺入经过它的动物的蹄子和人类的鞋底。窃衣(Torilis scabra)、鬼针草(Bidens pilosa)也不例外。星叶草(Circaeaster agrestis)的种子外形就如人们喜食的海参,只不过它表面的突起不是什么美味的参肉,而是硬而脆的倒钩,借助这些倒钩,它能轻易勾在经过动物的皮毛或人的衣物上进行散布。比起依靠风、依靠重力来旅行的种子,苍耳、蒺藜和星叶草们的方式的确在某些时候显得粗暴,甚至可以说为了远行简直不择手段。在生物界,我们一直倾向于将植物们视作一些老成持重的角色,它们是一个懂得观望、适应和等待的族类,但植物们实际上不过是一些将野心、暴力和侵略藏在矜持和内敛背后的家伙。例如有些植物在开花的时候就开始变为杀手,像狸藻和黄花草,其他如食虫草、茅膏菜、猪笼草、锦地罗等则从一开始就是个杀人如麻的家伙。在生存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美德和礼让可言,一切都是杀与被杀、利用与被利用。每一种本能都渴望返回它出发的地方,哪怕只是作为回声。而美德只能辨认出自己的同类,并不能辨认恶行。至于恶行,实际上只是本能的另一张面孔。
动物们也并不介意在运动的时候捎上这些小麻烦,尽管植物与动物的基本关系是吃与被吃。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在食物链的任何一端都没有友谊与友爱:细菌以上帝仁爱的生机为食物,大一点的生命以符合自身属性的细菌生命为食物,再大一点的蚯蚓以泥土中的细菌和草籽为食物,獾和兔子以蚂蚁、蚯蚓与小草为食物,鹰以老鼠和小鸟为食物,再大一点的动物如羊与狼、狮子根据种类的不同分别以植物和其他动物为食物,再之后是人类,为补充自己的气血精神以富含宇宙生机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物;之后,反过来,细菌又以食物链最高端的人类为食物,植物以细菌为食物……植物在其间不过是一个被反复食用的角色,不被食用的时候,它忙于光合作用,为各种高低等动物提供呼吸所需要的氧气。不过地球上能够长命百岁的却往往不是动物而是植物,大部分植物的寿命比动物长,科学家们分析,这是因为植物根部的某些组织干细胞对于DNA损伤不太敏感的缘故,这些细胞能够为植物保存着原始的完整 DNA 拷贝,在必要时可用于替换受损细胞。尽管动物也依赖相似的机制,但植物有可能以一种更为优化的方式利用了这一机制。植物的种子也比动物更能抵御恶劣的环境,它们的自愈能力更强,而且一旦情况不妙,它们就采取休眠的方式渡过危机。休眠时,种子里面所富含的营养足以让它们熬上很长一段时间。动物却没有这项能力,动物的种子,如果可以把卵子与精子称作种子的话,它们比动物的其他组织更加脆弱,对温度、湿度和其他环境更加敏感。为了保护它们,动物们一度用最深的腹部存放它们,用一种行为复杂的性交运动来让它们相遇,然后花上数月的时间,让它们在看到世界其他部分之前先秘密成长起来,在让它们拥有一些基本能力之后才降落到这个世界上,让它们看到光线,看到风,看到雨,看到危险、惊奇和各种无穷。而这一切,植物的种子们都是自己直接面对的。
表面上的一些现象很容易迷惑人。我们经常将脆弱性视作低等物种的首要特性,我们经常把植物们的一些行为视作有限的、低等的智慧,如像搭动物便车这类轻易就被人识破的花招就会让我们捧腹大笑,但植物们其实才是情节缓慢、窥破红尘、笑到最后的角色。一年又一年,它们站在那里,看着有着上百万个不同名字的动物,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死去而它们活着,在我们将其静默视作笨拙,将其世故视作懒惰,将其智慧视作骗局时,这些在细胞的精确、敏感、密度上与我们相似或者更胜一筹的物种,比我们更清楚:一切存在都是无缘无故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我们出生,我们死去,而世界的本来面貌并没有改变。
发射雨滴炮弹
生存技能:利用雨滴
生存等级:五星
福柯在《乌托邦身体》中写道:
每当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作者)醒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缓慢而焦虑地重新占据这个位置:一旦我的眼睛睁开,我就再也不能逃离这个位置。不是说我被它固定了下来,毕竟我不仅能够自己移动、自己改变位置,而且还能够移动它,改变它的位置。唯一一件事是:没有它,我就不能移动,我不能把它留在它所在的地方,好让我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我可以到世界的另一头。我可以秘密地藏身于黎明,让自己变得尽可能的小。我甚至可以让自己在沙滩上、在太阳下融化——但它总会在那里,在我所在之处。它不可挽回地在这里:它从不在别处。我的身体,它是一个乌托邦的反面:它从不在另一片天空下。它是绝对的位置,是我所在并真正肉身化了的空间的小小碎片。我的身体,无情的位置。
是身体将我们判了刑,让我们最终生活在这里或者那里。是身体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存活100年还是几天。也可以说,所有的魔法,所有的童谣,所有的诗歌都是从身体开始,反对身体乌托邦奏响的一个序曲。
对于菊花草来说也一样。
菊花草带着轻盈但无法改变的身体,几乎生存在从雨林到沙漠的任何地方。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拥有一个秘密武器——圆锥形的花朵,能够捕捉到微小的雨滴并且借助雨滴飞溅的效果来压缩并且弹射种子。菊花草每个花朵花壁的倾斜度可帮助雨滴的溅射速度达到最大化,圆锥形的弯曲度也能产生一种喷嘴的效果,使它的种子能够向一个方向集中喷射。
矮小,其貌不扬,没有漂亮的花朵,没有丰美的果实,这样的身体对于一株植物来说的确不那么走运。因为长得低矮,没法获取和利用更多的风能,使它们不能像其他植物例如斑叶兰那样,随随便便地就去它们可去的地方;没有漂亮的花朵用以吸引其他的昆虫接近,它们的种子也没法搭顺风车去往远处;没有可口的果实用来贿赂飞鸟,意味着生命中将不再有其他的意外发生。
但是,等等,还有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