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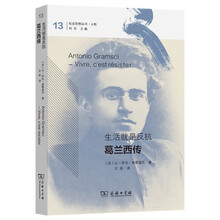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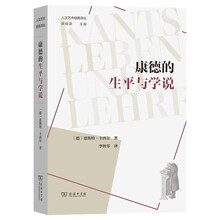
民国大先生金岳霖的一生,注定了是一段传奇。因为他的名士风,因为他的痴情。
本书叙述金岳霖在成长、情趣、交友等方面的经历,说出身,说成长,说游艺,说治学,谈爱好,忆故交,展现他真实的人生——学术成就卓然的哲学大师,天真烂漫如孩童,洒脱飘逸如名士。对爱简单而执着,一生痴情于才女林徽因,动人而神圣,一辈子“逐林而居”,终身未娶。
是真名士,自风流。
第十章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林徽因,一个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个曾经向往诗意浪漫生活的女子,一个体弱多病的女性,却能经受住艰苦的野外考察生活。一向优雅浪漫的她会和男子一样餐风宿雨,爬梁上柱。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出一种可贵的内在精神,一种坚忍与执着,一种自我奉献和牺牲的精神,一种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乐观自信的情绪。
即使在抗战期间,在颠沛流离的乱世里,这位美丽的知识女性也始终保持着从容、优雅与高贵。古都北平沦陷后,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梁林夫妇举家迁往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所有内迁学校集体联合办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梁林夫妇在昆明北郊龙泉镇棕皮营设计建造了一所住房。他们于1940年5月迁入新居。林徽因在致友人费正清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幽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金岳霖靠着梁家主屋一面墙,搭建了一间耳房,云南人叫“偏厦”,比正屋低矮一些,面积不足十平方米。最让人惊诧的不是这间屋子的矮小,而是它没有独立外开的门。也就是说,金岳霖每次出入必须穿过梁家的主客厅。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俨然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林徽因曾经在致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他们的家庭生活说:“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并记述当时的生活状态道:“轰炸越来越厉害,但是不必担心,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逃脱的机会比真的被击中的机会要多。我们只是觉得麻木了,但对可能的情况也保持着警惕。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在四川李庄生活时期,梁林夫妇生活非常困窘。
由于营养不良,林徽因的身体日渐消瘦,经常发烧卧床不起。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最后山穷水尽,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又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笔和金表送到当铺,换回两条草鱼。即便如此,夫妇俩仍然不改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梁思成提着两条草鱼回家,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盼望着它们生下蛋来,好给林徽因补养身体。老金是文化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总布胡同时代,他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医生“助产”的笑话。到了昆明后,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汪曾祺也回忆:“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也有很深的印象:在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呀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
果然,金岳霖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好,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难得吃到鸡蛋的人们十分开心。1941年7月,金岳霖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叹息:“这里的天气总是变化无常,每次理完发我都要得一次感冒。我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增减衣服的状态,时时处在或是刚刚遁入感冒的忧郁中,或是迎来刚刚摆脱一次感冒之后的愉悦……很显然,这实在不是一个能让徽因恢复健康的地方。”
金岳霖的到来无疑给林徽因带来极大的慰藉和欢欣,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快乐地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林徽因写罢给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个人看,老金在信后补充道:“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也补充道:“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7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一位当代青年女作家读过这三封信后评说道:“三个人都是妙人儿,而且必须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时才能如此有趣,如此的澄澈、明朗,就像三个未经世事的同学,依旧走在青春的光影里,而远景,是战火与硝烟。”梁林夫妇在李庄生活了6年。这期间除去到美国讲学访问,金岳霖也一直在昆明和四川李庄之间奔波。
1938年3月初,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金岳霖给费正清夫妻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
“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
他说到林徽因,在长久离别之后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金岳霖还说:“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林徽因则是高兴地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这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写作《中国建筑史》。老金也借营造学社的一张白木桌子,开始重新写他那部皇皇巨著《知识论》。每天下午三点半,他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弄一个茶壶喝起下午茶来。病中的林徽因也把行军床搬到院内,与大家一道喝茶聊天。老金便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林徽因的病榻前,或者端上一杯热茶,或者送去一块蛋糕,或者念上一段文字,然后带两个孩子去玩耍。
金岳霖一辈子单身。他爱着林徽因,也爱着林徽因的全家,他后来几乎一直和梁家住在一起。
据著名女翻译家文洁若回忆:“在静斋宿舍里,高班的同学们经常谈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伉俪。原来这些同学都上过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才随校从昆明复员到北平,然后根据各人志愿,分别插入清华、北大或南开。由于是战时,西南联大师生间的关系似乎格外亲密,学生们对建筑系梁、林两教授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当时传为美谈的是这对夫妇多年来与哲学系金岳霖教授之间不平凡的友谊。据说金教授年轻时就爱上了林徽因,为了她的缘故,竟然终身未娶。不论战前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还是战后迁回清华之后,两家总住紧邻。学问渊博、风趣幽默的金教授是梁家的常客。他把着手教梁家一对子女英语。那时,大学当局对多年来患有肺病的林徽因关怀备至,并在她那新林院八号的住宅前竖起一块木牌,嘱往来的行人及附近的孩子们不要吵闹,以免影响病人休息。
在静斋,我有个叫谢延泉的同屋向学,她跟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十分要好,曾到梁家去玩过几次。她说,尽管大夫严禁林徽因说话,好生静养,可病人见了来客总是说个不停。谢延泉还亲眼看见金教授体贴入微地给林徽因端来一盘蛋糕。那年头,蛋糕可是罕物!估计不是去哈达门的法国面包房就是去东安市场的吉士林买来的。
虽然我被分配到一位姓王的教授那一班,可我还是慕名去听过几次金岳霖的课。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教授同车。车上的金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旁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他们在数西四到西直门之间,马路旁到底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必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女梁再冰和梁从诫了。
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他们二人都摆脱了凡夫俗子那种占有欲,共同爱护一位卓越的才女。金认识林徽因时,她已同梁思成结了婚,但他对她的感情竟是那样地执着,就把林所生的子女都看成自己的孩子。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当时,梁再冰正在北大外语系学习,梁从诫也在城里的中学住宿,金岳霖可能是进城陪这两个孩子逛了一天,再带他们回家去看望父母。”
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他们每个人的学识、涵养和人格使得这种情感问题处理得很妥当,达到一种令人钦佩的平衡与和谐。林徽因身上有着生性敏感的诗人气质,让她容易动情。可是,她本性善良加上清醒的理智,让她不可能做伤害梁思成的事情,也不可能轻易辜负纯洁的感情。梁思成更是坦荡君子,相信妻子和朋友,因此表现出难得的气量和风度。最难能可贵的是金岳霖,他深深地爱了林徽因一辈子,发乎情,止乎礼,终身未娶。他一辈子都站在离林徽因不远的地方,默默关注她的尘世沧桑,苦苦相随她的生命悲喜。静静地付出,默默地守候,不奢望走近,也不祈求拥有;即便知道根本不会有结果,也仍然执着不悔。理性、克制、温和,毕生一以贯之。
世间精于理者未必不深于情。在金岳霖那里,爱情无疑是一种使人向善、向上的圣洁力量。这不禁让人想起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这样的境界并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金岳霖的老朋友、老同事吴宓,当年苦苦追求一代才女毛彦文,不惜与发妻离婚、不顾社会舆论,成为一大奇闻。后来,33岁的毛彦文没有答应他不说,竟然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已经66岁。吴宓痛苦不堪,一口气写了38首“忏情诗”来表达他的悲凉心境。其中有一首是:“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他不但在《文学与人生》课堂上公开朗诵自己的这些情诗,还发表在报纸上。一时舆论大哗,认为吴宓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
这些也让毛彦文陷入困窘,让吴宓在清华的同事、朋友看不下去。于是教授们公推金岳霖去劝劝吴宓。金岳霖劝吴宓:“雨僧兄,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是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儿。这是私事,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去宣传。比如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拿去宣传。”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们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忙解释:“我没说你们的爱情是上厕所,我说的是个人的私事不宜宣传得尽人皆知。”而吴宓心头怒气无处发泄,正好把金岳霖痛快地大骂了一顿。金岳霖失言在先,不知如何是好,唯有沉默而立,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任凭吴宓骂了半天。
后来金岳霖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虽然劝说无效,但他内心对老朋友这样没有节制、痴气十足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有人曾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友情可言。其实,这男女“友情”也许比较暧昧、比较模糊,无法完全准确地拿捏,但是,理性与信任无疑是这种友情得以存在的前提。当事人内心的坦诚、包容,使得他们能够泰然镇定、理智从容地对待这种感情。第十一章一身诗意千寻瀑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1955年4月2日,一代才女名媛林徽因病逝于北京,离开了这个她深深爱过的世界。
林徽因的离世让一向冷静而理智的金岳霖悲痛万分,久久不能释怀。第二天,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周礼全到办公室看他,金岳霖先不说话。当整间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岳霖先是沉默,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就号啕大哭。周礼全后来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周礼全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这才把他送回家。
周礼全说:“这次痛哭,是他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一种特殊感情的迸发,是深沉的痛苦,是永恒的悲哀,是纯洁的人性,我十分理解他这种感情,我十分尊重和欣赏他的这种感情。”
三十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岳霖慢慢地回忆说道:“林徽因死在同仁医院,就在过去哈德门的附近。对她的死,我的心情难以描述。对她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极赞欲何辞’啊!”
林徽因去世那一年,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虽然林徽因头上还顶着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个头衔,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
亲朋好友们送的挽联中,只有金岳霖的挽联别有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引人注目: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富饶。然而林徽因去世的这个四月天,却让他终生难忘。他回忆当年参加林徽因追悼会时的情形说道:“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
……
第一章 少年神童金龙荪
第二章 一心要学“万人敌”
第三章 同居的神秘美国女子
第四章 清华园阁楼里的“哲学动物”
第五章 哲学家的幽默与风采
第六章 金岳霖的读书治学之道
第七章 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
第八章 “道超青牛,论高白马”
第九章 让人惊艳和痴迷的女子
第十章 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第十一章 一身诗意千寻瀑
第十二章 最懂女性的人
第十三章 非常年代的思想转向
第十四章 剪不断的师生情
第十五章 金岳霖的“朋友圈”:回望那些远去的背影
第十六章 一个纯粹而丰饶的生命:顽童哲学家
尾声 永远的“金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