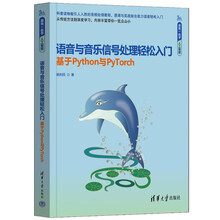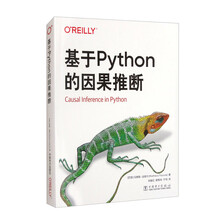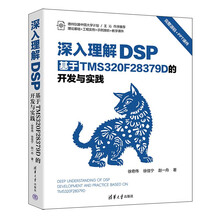其次,在某种程度上,威利斯和拉德威生硬地将学童和郊区女性的经验纳入其政治和理论结构中。因此,他们可能无法接受那些男孩与女性生活世界中的某些肌理及细微差别,尤其是那些会对其结构形成挑战的部分,例如乖乖男孩的经验,或罗曼史中令人兴奋的愉悦。这种生活经验在转换过程中的“遗落”或丧失正是新民族志对传统研究形态提出的批评。传统研究认为“学者”对人的了解多于人本身,在其最终的学术成果中,阐释研究对象的部分还不如阐释推动研究的理论及政治计划,这一点使得他的研究一直成为新民族志的批评对象。
再次,在威利斯和拉德威的研究中,有一种维度颇为有趣。对经验的研究方法是将经验置于其他地区及活动更为广大的社会景观之中,两人的研究均指向了这种新的研究途径。威利斯和拉德威都将其研究的特定主题(即学校行为及阅读罗曼史)语境化,采用的方法则是诉诸其他观点:威利斯诉诸工厂,而拉德威则诉诸性别化的人际关系。这种做法扩展了研究范畴,因为从其他视角来看,被研究的对象似乎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男孩最终投身工厂工作,由此看来他们在学校的恶作剧不再那么具有“抗拒力”。即使拉德威并未研究那些女性与伴侣的关系,她也暗示了一种问题,这种问题同她们阅读理想的、能付出关爱的男主角时所展现的“抗拒”本质有关。
从多个角度审视一个现象,这种做法类似最近的多观点的(例如多地点的或多重声音的)研究途径。本章后面部分会稍微提及这种途径,并会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尤其是第九章中加以详述。然而,多地点研究和威利斯、拉德威的研究存在差异,威利斯及拉德威常会以结构性的观点,将一个地点(工厂及女性的人际关系)设定为比另一个地点(学校、阅读罗曼史)更“现实”或更重要。建构不同地点的阶层关系的做法否定了特定活动或生活范畴的重要,因而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说,若没有制造出异性恋的亲密关系(拉德威没有这样说过,因为她并未研究史密斯敦女性的关系,但可以参见拉德威1988年的著作)的改变,来自消费媒体(例如罗曼史)的颠覆性愉悦便缺乏意义。研究从不同观点审视某一现象时,将这种现象的不同面貌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解释其不同的、有可能是抗拒性的压抑与受压抑维度,这种途径会更有成效。要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及地点的更广阔语境中来审视抗拒,这是这种途径留给当代文化及社会研究的贡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