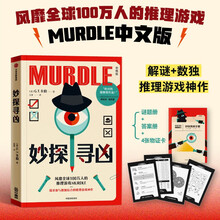“我听说过你那件可怕的事。”马蒂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佩勒姆没有扭过头来看他,他正开着一辆温尼贝戈①酋长43回城。刚才他们在离这条路一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户农舍,他们主动提出要给房主一千三百美元,借用他家的院子拍两个场景,前提条件是他不介意他们这两天把那辆停在车道上生了锈的橙色尼桑车换成联合收割机。房主听后颇为震惊,他说,为了这笔钱,哪怕他们要求他把那辆车吃掉,他都没意见。
佩勒姆告诉他没这个必要。
“你做过替身?”马蒂问。他嗓门很高,说话时带中西部口音。
“对,做过替身。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部电影是讲什么的?”
“呃。”佩勒姆摘掉那副五十年代休·海夫纳①风格的墨镜。秋日的天空如纯冰一般明亮。半个小时前,天色曾经暗过一阵,而现在,秋天的午后犹如冬日的黄昏。
“是一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马蒂说。
“我从来没为斯皮尔伯格工作过。”
马蒂想了一下。“没有?我怎么听说是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反正,里面有一个场景,有一个家伙,你知道就是那个主角,在桥上开摩托车,炸弹在他身后不断地爆炸,他在弹片前头开摩托,疯狂得像个婊子养的。但就在那时,一颗炸弹在他身下爆炸,桥倒塌的同时,他必须飞起来,他们本来想用假人,因为替身指导不想让他手下的人干这个活儿,于是,你骑上摩托,让特技组导演开机。你就这么做了。”
“嗯哼。”
马蒂看着佩勒姆,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接着,他大笑起来。“嗯哼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做过没有?”
“对,我记得有这么回事。”
马蒂的眼睛骨碌碌转,看着窗外远处的一个斑点,那是一只鸟。“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他回过头来看佩勒姆,“我还听说,事实上,你没被炸飞,桥塌的时候,你紧紧抓住了钢索。”
“嗯哼。”
马蒂还在等待。对一个应该给你讲战争故事的人讲战争故事并不好玩。“然后呢?”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你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佩勒姆把手向下伸,拿起夹在两只破旧的棕色诺科纳靴子中间的莫尔森啤酒。环顾了一下红彤彤黄灿灿的秋天的乡下,确定附近没有纽约州骑警后,他举起酒瓶,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我很蠢。特技组导演把我解雇了。”
“可是他们用那个镜头了吗?”
“不用不行。桥已经被他们炸光了。”
佩勒姆踩了一脚已经磨损的油门踏板,加了一挡。发动机反应迟钝。老发动机把沉重的野营车向山上推时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马蒂二十九岁,骨瘦如柴,左耳朵上戴了一只小金环。他长了一张圆脸,皮肤光滑,眼皮仿佛直接和心脏相连,只要脉搏加速,他的眼睛就会睁得很大。佩勒姆比他年长,也是个瘦子,但与其说他骨瘦如柴,不如说他是个精壮的汉子,且肤色偏黑。干草一般的胡子中点缀着斑白,他是从上星期开始留胡子的,现在已经厌倦了。遮住他灰绿色眼睛的眼皮从来不会抬得很高。两个人都穿着牛仔服——蓝色的牛仔裤和外套。马蒂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佩勒姆则穿了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衫。这身衣服,再配上尖头的皮靴,让佩勒姆看上去是个十足的牛仔,如果有谁会对他这身装扮发表意见,那通常是女人,他会告诉她,他和野比尔希科克是亲戚。这是真事,不过,真实得有点复杂,这个故事被他篡改了很多遍,现在连他自己都记不清这个枪手怎么就变成他的祖先了。
马蒂说:“我想做替身。”
“我不这么认为。”佩勒姆说。
“不,会很好玩。”
“不,会很痛苦。”
过了几分钟,佩勒姆说:“我们已经搞定了墓地、一个城市广场、两个谷仓和一户农舍,以及很多条路。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马蒂翻开一个大笔记本。“一片很大很大的田地,要特大的那种,一个殡仪馆、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房前有一个院子,院子大得可以举办婚礼,一个五金店、一堆乱七八糟的室内装饰品。该死,这两个星期我是回不了曼哈顿了。牛我是看烦了,佩勒姆。我简直对牛厌烦透顶。”
佩勒姆问:“你驯过牛吗?”
“我是从中西部来的。那里的每个人都会驯牛。”
“我就从来没做过。不过,我想尝试一下。”
“佩勒姆,你没驯过牛?”
“没有。”
马蒂摇了摇头,看来他真的很吃惊。“天哪。”
他们已经在纽约州克利里的州际公路上晃悠三天了。温尼贝戈车记录的行车里程是二百英里。他们开过山丘,山上长满疙疙瘩瘩的松树,开过陈旧的牧场,以及色彩柔和、样式简单、小方盒子一般的房子,车道上停着皮卡,街上停着汽车,挂在根根长线上风干的衣服已经变得僵硬。
三天的时间里,他们穿过薄雾、浓雾、九月的树叶卷起的黄色风暴和好多场下得透透的雨。马蒂望着窗外。他有五分钟没说话。佩勒姆想:沉默是金。
马蒂说:“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了吗?”
这个孩子的思维犹如饥饿的乌鸦到处乱飞。佩勒姆根本猜不到他的心思。
“我在《战争的回响》剧组做过助理。”他继续说。
那是一部投资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关于越战的电影。当时,佩勒姆不想为这部片子选景;现在,他不想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他知道,即使碰巧去了洛杉矶的录像城,他也不会租这部片子回家看。
马蒂说:“出于某种原因,这部片子没在亚洲拍?”
“你是在问我吗?”
“不是。我是在告诉你。”
佩勒姆说:“怎么听着像是你在问我。”
“不。他们决定不在亚洲拍。”
“为什么不?”
“这不重要。总之他们就是没在那儿拍。”
“明白了。”佩勒姆说。
“是在英格兰拍的,康沃尔郡。”马蒂把脑袋歪过来,那张椭圆形的大脸上绽放出笑容。佩勒姆喜欢热情,但热情总是与话痨相伴。你不可能拥有一切。“好家伙,你知道英格兰有棕榈树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棕榈树不管怎么说,布景师搭建的所有场景都令人难以置信,军事基地、战壕什么的。我们早上五点钟起来拍摄,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自己在英格兰,也知道这不过是个电影。但所有的演员都穿着戏服——军装,睡在掩体里,吃着配给的食物。导演就想要这个效果。我告诉你,伙计,站在一边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恶心。”他琢磨了一下这个词用得是否准确。最终,他认为很准确,于是又重复了一遍,“恶心。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他沉默了。
佩勒姆拍过几部战争题材的电影,但此时他一部片子也想不起来。现在他想的是,他们刚到这里一天,野营车的玻璃就被砸出一个玫瑰花饰。温尼贝戈的玻璃很结实,瓶子穿过玻璃一定费了不少力气。瓶子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再见。”这些年,这辆野营车遭受过各种各样富有创意的破坏,但只有这次令人心烦得莫名其妙。佩勒姆发现,搞破坏的人很有先见之明,没把纸条从前挡风玻璃那边砸进来。他们想确保温尼贝戈开出城时,景色依旧可以一览无遗。
他还发现,投射物是瓶子,而不是石头,瓶子里很容易装上汽油,也可以装一张经过认真书写的纸条。
约翰·佩勒姆想的是这个。不是替身,不是战争电影,不是热带英格兰不祥的黎明。
“有点冷了。”马蒂说。
佩勒姆把手伸向仪表盘上的暖风控制调高了两个刻度。随即,温暖的空气带来的潮湿的橡胶味充满了车厢。
佩勒姆的靴子踩到碎玻璃碴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把它们踢到一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