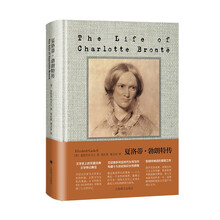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尧辅(李公佐,字尧辅)!久违啦!”欧阳修紧走上前,拉住了李公佐的双手。李公佐反手握住欧阳修的手,也激动得不得了。“走,我们到内堂说话。”说着,李公佐拉着欧阳修,两个人一起往内堂而去。
听说欧阳修要当父亲了,李公佐哈哈大笑:“永叔,你知道吗?当初跟我们一起在园子里玩的那些小子们,都已经当爹啦!他们的孩子都有你刚来汉东时那么大了。”欧阳修一听,也笑了:“是啊,从我们认识到现在,算一算都过去七个闰年啦。小时候的事现在想想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顺便指出,欧阳修所说的“算一算都过去七个闰年”的话,是需要天文历法知识才可以理解的。我国自从科学设置闰月后,周期是十九年七闰。这在古代是常识,文化人当然更清楚。因此欧阳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俩认识都十九年了。欧阳修当年二十七岁,认识十九年,他和李公佐认识时才八岁。欧阳修是四岁时随母亲郑氏到随州投奔叔叔欧阳哗的。八岁应该是上学的年龄。刚刚上学便认识李公佐,或许二人是小学同学。
经过一座书楼的时候,欧阳修停下了脚步。李公佐见欧阳修站下了,他也停下了步子。他看看欧阳修,又看看书楼,笑了。
“永叔,还记得你从破筐里找到‘宝贝’那件事吗?”欧阳修脸一红:“尧辅说笑了,但那东西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李公佐所说的“宝贝”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还得从欧阳修小时候说起。
那时候,小欧阳修经常到李家借书读,有一次他在东园这座书楼找书,不想,却在墙角发现了一个破竹筐。筐里堆满了破旧的书籍残卷,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欧阳修好奇心起,就把筐里的书一本本拿出来瞧。瞧着瞧着,欧阳修眼前一亮:“呀,这不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写的《昌黎先生文集》吗?’’他又在筐里翻了翻,一共找到六卷。打开一看,这书可有年头了,纸张都有些揉烂了,里面还夹着不少脱落下来的书页,正面、反面都有,也没个次序。小欧阳修找了一篇仔细一读,发现韩愈的文章写得深厚雄博,别有深意,自己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但也知道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看了一会,欧阳修实在舍不得放手,就把其他旧书整理一下又放回筐里,单抱着这六卷文集走出书楼。见到李公佐,欧阳修红着脸说:“尧辅,这些书能借我拿回家去读吗?’’童年的李公佐是个爽快的小孩,知道欧阳修家境贫寒,总存了助人为乐的心。
他见这六本书残破不堪,而好朋友欧阳修却像抱着稀世珍宝一样爱不释手,就笑着说:“你如此看重这些书,就送给你吧。”欧阳修喜出望外,连连道谢。
那时,北宋社会的读书人并不推崇韩愈的文章,而是在极力模仿和学习杨亿和刘筠的文章,并把这类文章称为“时文”。杨亿和刘筠都是宋初的知名学者、大臣,更是北宋“西昆体’,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西昆体”的诗歌大多是学晚唐诗人李商隐,讲究整饬典丽,但没什么思想内容,跟时代和社会生活有点脱节。
说白了,就是不能与时俱进,“时文”也是如此。但当时的北宋社会从上到下,从官僚到士子都好这一口。只有“时文”作得好,才有望考取功名、扬名文坛甚至荣夸当世。就连欧阳修也不能免俗,狠下了两三年工夫研习“时文”。
天圣元年(1023),十七岁的欧阳修带着满脑子的“时文”知识,第一次参加了随州的州试。那次考试的题目是《左氏失之诬论》,欧阳修文章中有一句“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因为不符合官方规定的韵,结果名落孙山。
回到汉东,欧阳修从床底下翻出小时候从李家找到的那六卷《昌黎先生文集》。反复读了几遍,欧阳修觉得既郁闷又羞愧,心道:“学者只有写出这种文章才算是做学问做到家。世人怎么就不推崇韩愈的文章呢?别说别人了,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抽不出时间去读他老人家的文章,只能自己时不时在心里念叨一下,认为只有中了进士、谋到一官半职、有了俸禄才能奉养母亲。将来我若做了官,一定也要做出这样的好文章,一偿夙愿。”三年后,二十岁的欧阳修终于通过了州试,并于次年(1027)由随州举荐参加了春天举行的礼部贡举,没想到又一次落榜。
天圣六年(1028),欧阳修带着用“时文”体写的《上胥学士偃启》,只身前往汉阳拜见翰林学士胥偃。向来以严谨著称的胥偃对欧阳修的文章赞不绝口,并留他住到家里,细心指导他作“时文”。这年冬天,年轻的欧阳修跟随胥偃来到了繁华的汴京,并被他引荐给京城里的知名学者、达官贵人。第二年,欧阳修先后在国子监考试、国学解试中获得第一名,第三年又在礼部考试中获得第一,并在崇政殿御试中获得甲科第十四名的好成绩。P9-P11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