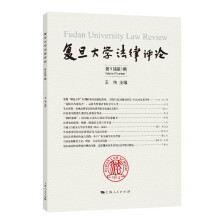《法学家茶座(2016.4 总第48辑)》:
治统与道统,这对概念对认识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关系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顾炎武曾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维护“天下”比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更重要,而这个天下就是“仁义”的道统。这几乎是在呼应孟子的说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看来,。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是殉国,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则可以说是殉道了。
在告别王朝更替、进入共和之后,随着儒学统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中的崩溃,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话语体系被快速遗忘,而一种新的“道统”在逐渐形成,它的核心是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在这一“新”的话语体系里面,有着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相通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只是很少有人(尤其是今人)去融通两个体系。今天即便想做这个事情,“古”“今”“中”“外”这四个字,任一都是极难攻克的。
比之于“新道统”,旧道统有个提倡值得今人记取,这就是对“士”的社会责任的高度期待。孔孟以降,每个儒学大家都给读书人以极高的要求,而传统的读书人大多也都秉持仁义的信念,既作为行动的指南,又作为心灵的追求。当然,读书人做了官之后大多会变样,因为两个体系对他的制约是不同的,现实体系的制约程度和诱惑力远远大于信念和教条。如今的中学教科书会称他们为“卫道士”,如《红楼梦》里的贾政。在新旧更替的年代,他们确实是被革除的对象,因为他们完全不符合所谓“新的时代”。然而,即便他们中那些假仁假义之辈,起码还忌惮社会舆论,在意自己的身份;不像眼下的若干等等,面子、里子俱是坏的,连“体面”、尊严都省了,彻头彻尾甘愿做流氓。
当下的法律研究,无疑是彻底拥抱“新道统”的。然而,“新道统”之于当今之法学界,不过如浮土一般,一则只能长出些杂草,二则经不起风吹。一言以蔽之:有道无统。在旧道统那儿,读书人以仁义为精神追求,是发自内心地向往,即便后来很多人会忘掉,起码年轻时基本上都信。而在“新道统”这儿,写出那些字眼的人自己都未必信。文字中的慷慨激昂,难以触动读者对“道”的认同和接受;成篇的引经据典,难以掩盖思想认识的贫乏和空洞。很多人喜欢谈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在谈“信”。不过,如果谈与法律有关的信仰,还是谈对“法”的信仰更好,因为“法”不仅仅是制定法,而是超乎其上的正义。
吊诡的是,何为“正义”?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反对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在大多数情形下,对某一个事情是否合于正义,也会得出基本一致的判断,然而对有些事情的判断就未必了,尤其是涉及民族、文化、宗教、政治以及其他重要利益的冲突时,何为“正义”常常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国传统社会的正义观也有其独特性,比如涉及家庭伦理方面,和西方的看法、和今天的看法会有一定的冲突。在谈及自由、人权和民主等与正义相关的价值的时候,也会发现不同文化对其理解的差异性。所以,即便说拥抱“新道统”没有错,那么,在理解和界定其内涵时,要考虑文化上的差异性。说得激烈些,应当建设和拥抱的是中华的新道统,而非抽象意义上的“新道统”。目前的一些法律研究成果,以外来的价值观作为判断中国问题的标准,就忽视了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而且始终摆脱不了对“文化他者”的依赖性。一些读书人离开了英美德日“文化奶妈们”,就不会讨论和研究问题了。如此,怎么可能形成具有中华特质的法律文化呢?或许会有人反驳:不是全球化时代吗?呵呵,那种全球化不过是文化的新殖民主义。我们难道要用英美德日的脑袋思考中国问题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