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导的年代
如果邪恶以正义和权威的声音说话,
如果邪恶以仁慈和有理的声音说话,
如果邪恶以适度和经验的声音说话,
来帮助我们避免痛苦。
如果我们真的绝望,
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铤而走险。
如果我们真的遭遇痛苦,
让我们看到我们确实陷入了痛苦。
如果我们因为恐惧而畏缩,
让我们知道那是因为绝望、痛苦和恐惧。
所以我们不能胡思乱想,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启示,
已经找到了进出的大道,
仅此就已经改变了我们。
奥地利诗人艾利希·傅立特《夜之祷告》
(PrayeratNight)(一九七八年)
是什么决定和影响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行为?是时代的精神吗?这应该怎么来进行界定?本作者认为,答案是在一个反革命当权的国家及其联盟的特定社会结构内,人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过程。那又该如何解释标志着二十世纪结束时的大规模转轨?大批大批的政治家、学者、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全都集体接纳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更不用说那些搭便车的野心家了。凭借敏感的本能,他们明白,政治文化生活的决定趋势是随大流。于是他们隐藏了所有的想法,摇身一变表示附和。这一切产生了其自己的心理和语言。支撑全球新秩序(NewOrder)的柱子几乎被看作是神圣的制度,其权威来源于自身存在的这一事实:全球公司是有益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球公司,它之所以是一个全球公司,是因为有益的。现实中,这个逻辑就是北约(NATO)的东扩和美国设在一百二十一个国家的军事基地。
广义上说,所有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垮台,加上美国与共产党阵营(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九一年)的冷战和热战的结束,对许多当时依然赞同左翼的人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抱什么幻想的人,也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就像是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王朝复辟之后,很少有人会公开宣称“我是一七九四年的人”——司汤达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人物,他认为国王路易十六遭处决的那一年是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关键时刻——所以对许多欧洲人来说,一九九一年之后再也不可能说“不管怎么样,我依然是一九一七年的人”。后者还会很快导致有些人得出其他的结论:“我决不可能成为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妇女”,或者“我一直认为,英国工党政府一九四五年对矿山和铁路实施国有化是错误的决策”,或者“法国人对国家的痴迷是从维希那里接管政权”,或者“左翼在西班牙和希腊内战中失利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此等等。
与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形成对比的是,南美洲的忏悔者数量更少。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拒绝反对古巴革命。而且甚至那些尖锐批评卡斯特罗的人士,也不赞成对他实施暗杀。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著名人士,其中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但这些人并不能代表在西方学术界和在全球新闻界服务的大多数拉丁美洲人。他们“成熟”了,沦落了,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出卖了灵魂。如果不再学习,就不能获得认可。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是绝对的。华盛顿共识成了霸权主义。新秩序的两个主要理念是:一、从现在起到地球爆炸,资本主义的新模式是组织人类活动的“唯一”方法;二、西方打着自己所谓的“人权”标准旗号,粗暴侵犯主权国家。这些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内外政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像传染病般地散播开来。幻想被出卖,希望遭丢弃,导致了对过去的痛苦回忆,增强了个人的野心,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识时务者发达了。
第一个理念的结果,是一个空心的民主制度,是政党体系的持续衰退。这在西方更为明显,在印度、巴西和南非也有。政治区别耗尽之后,党派成了空壳,原来旨在帮助政治精英的机制,转而去追求权力和财富。党员数量越来越少,但在一些职业人员和政治地位相等的广告工作人员的操持下,仍有一个微小的基层网络在运行。上世纪,赫伯特·马尔库塞受到了广泛的嘲笑,因为他预计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势,正在开创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人类也在由此而大量繁殖,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冷漠和分化的社会。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加速了这个过程。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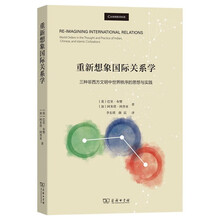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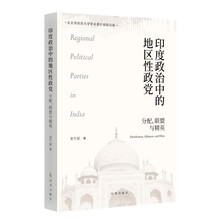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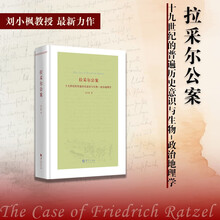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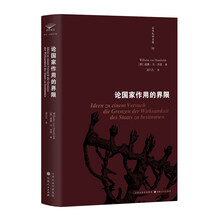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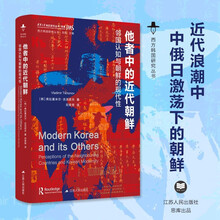
——英国《观察家》杂志
文笔生动,耐读好书。
——《伦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