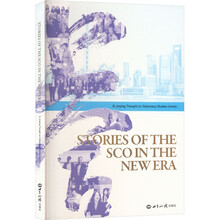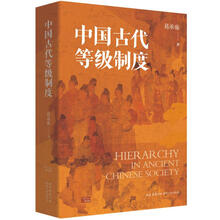《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
第一时间:记忆中只剩下一面光明的墙
第一个时间段中出现的是一段记忆。它是最初的记忆,带着伤感,也简单得令人失望:“就是这么一幕简而又简的布景……为了重演我更衣上床的那出戏,这些道具是少得不能再少了”;“似乎只有晚上七点钟这一个时辰”。这个记忆涉及的是“我”童年晚上七点钟的一段记忆。童年时代的小楼有两层,但在记忆中它只变成了一面墙,楼上楼下融成“一面光明”。这面墙作为一个断裂横在第一部“贡布雷”卷的“一”和“二”两部分之间。在记忆中,贡布雷的其他一切都死去了。“倘若有人盘问我,我或许会说贡布雷还有别的东西、别的时辰。但,那将是我有意追忆、动脑筋才想到的一鳞半爪。”这意味着“其他一切”并不重要。
在这个被简化的记忆中有个人物叫斯万,作者说他是“无意中造成我哀愁的祸首”。因为斯万的来访使母亲不能像往常一样,在临睡前给他一个晚安吻。这段故事很快就会被忘记,溶解在玛德莱娜点心和茶水之中。
而这面墙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五部《女囚》当中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带有悲剧色彩——我现在用的正是互文性解读。《女囚》中有个人物叫贝戈特,这面墙是在他去世前的场景中出现的。贝戈特是个作家,他和叙事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重影。贝戈特在荷兰画家弗美尔(Vermeer)的一幅画作中看到了“一小面黄色的墙”,在此之前他完全记不得有这面墙。弗美尔的这幅画作被评论家称为“一幅精致的中国画,其自身的美已经足够”。你们看,从童年走到母子中间的斯万,又走到作家贝戈特,然后到弗美尔的一幅作品,而作品中的墙因为时光的痕迹而使人想起中国画……记忆就这样曲折缠绕。这时,干涩无用的艺术(包括贝戈特自己的艺术)过渡到了伟大的艺术(弗美尔的艺术):在这幅杰出的作品前面,贝戈特觉得无地自容,晕头转向。贝戈特自己说:“我的最后几部书太枯燥无味了,应该过上几道颜色,让句子自身拥有美丽,一如这一面黄色的墙。”因为普鲁斯特还很善于揶揄,所以他写道:“贝戈特不知道是因为刚下肚的土豆没能消化,还是因为遭到这'一小面黄色的墙'的一击,就这么倒在地上,离开了人世。”所以,这个打击既是一种精神的打击,也是一种身体上的打击(可能是因为消化不良造成的)。许许多多的感觉都集中在这一个打击里面,这就出现了我们两天前讲过的文本意义的双重性:百感交集的时刻,是艺术之美达到巅峰的时刻,也是死亡来临的时刻。
而普鲁斯特并不害怕其他艺术的挑战。我们知道普鲁斯特的句子很长,但这种长句里面有很强的音乐感与画面感。故事接下来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让弗美尔的那面小墙也为之逊色。我们提到了“死亡”(过去的死亡,除了那“一面光明”,“孤零零地显现在茫茫黑暗之中”):它连接着贝戈特的离世,亦即作为非普鲁斯特式的作家的死亡;它也连接着童年难以重现的记忆的死亡。两种死亡通过“一面墙”发生联系,而与此相对的是艺术的力量。在这段文本中,接下来要展示的,恰恰是艺术的力量:它战胜了死亡,令童年的记忆重现。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感觉的铺设,童年的所有美好,被安置在了一块点心的世界。
……
展开